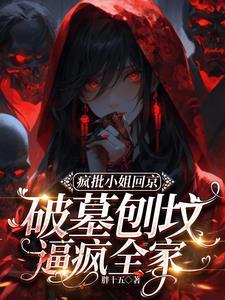02小说网>让你代班,没让你中兴大明 > 第119章 比如襄王殿下不用七步就能找出许多例子(第1页)
第119章 比如襄王殿下不用七步就能找出许多例子(第1页)
这……此言一出,全场静默。毕竟这不是有可能,是太有可能了。升斗小民管什么国家大计?只打自己的小算盘。一亩地种稻子能得两石,不过纹银一两。但同样一亩地,可产十几石桑叶,少者也有六七石。多则纹银五六两,少也有二三两。数倍差异下,种稻还是种桑?而且,桑树四年起科!程,臣自不必多言。至于别的,陛下文韬武略,英明无匹。不过……”殿下皱眉,似有些肺腑之言不知当讲不当讲模样。朱祁钰当即表示愿闻其详。然后,他就听到了襄王对于户籍事的担忧:“土木之变后,上……正庶人被掳,贼兵虎视眈眈。内外交迫下,陛下事急从权倒也无可厚非。”“但如今,刀兵已息,天下承平。您这权宜之计,是不是也该停停了?”到底户籍划分虽严了些,但也是为了皇朝稳定。民务稼穑、军保家国。正该各安其分,各尽其责,乱了户籍就容易乱却根本。比如?襄王殿下都不用七步,就能找出许多例子!“若商为良籍,不禁科举。以其家财,自然能购买更多书籍、延请名师为自己答疑解惑,普通耕读传家的考生怎能比过?长此以往,寒门更难出贵子。若庙堂之上皆商人子嗣亲眷,难保不为私利而坏大义。”“军户辛苦,闲时种田,战时上阵杀敌。但若军户都成民籍,那日后又谁来保国呢?”“士农工商,说来耕读传家,实际土里刨食。若能从商,轻轻松松赚得许多银钱,谁还愿意苦巴巴种地啊!”朱祁钰仔细瞧着,他家皇叔确实一脸凝重,特别担心的样子。十分真诚。那他可更要倾耳细听了。襄王殿下拱手,把礼仪这块拿得死死的:“谈不上什么高见,只臣一点蠢念头罢了。自大明立国以来,太祖便行屯田之法,寓兵于农……”不愧是经历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与如今景泰五朝的老王爷,对各种相关政策烂熟于心。讲得那叫一个清晰分明。且只忧国忧民,勇敢而又认真地指出朱祁钰哪方面的安排不够恰当。让他说提建议,他却半点不沾的。只道朝中人才济济,群策群力之下,定能想出妥善的解决方案来。主打一个关心,但不逾矩。老狐狸一只。但朱祁钰的口号就是绝不错过任何一个有用之才,就连夺门之变的核心人物徐有贞都被他派去修河堤,瓦剌降卒都得做苦力。更何况是他原就准备要化负担为助力的宗室们呢?遇上了,就绝不错过。皇帝陛下再度离席,执晚辈礼,满眼真诚:“襄王叔莫要太谦,您刚刚这一席话,胜过侄儿苦读十年书。朝中何人,能比得上您更博学多闻、更关心咱们大明和您侄儿我呢?”“好皇叔,您就多费费神,好好点拨点拨侄儿吧!”“您知道的,早年侄儿也跟您一样,有兄长为靠,也用不着操心江山大事。可谁料想着……”唉!朱祁钰长叹,满脸哀伤。襄王跟诸王与群臣们赶紧仔细宽慰。说些个皇爷仁至义尽,堪称国朝第一好弟弟,是正庶人身在福中不知福。非但不知感激,还怙恶不悛,做下犯上作乱之事。才逼得皇爷这般心善之人也不得不为了大明江山稳固故,将其正法的话。朱祁钰这才释然些,但仍说自己年轻经验少。陡然间成了这万里江山的主人,真真朝乾夕惕。生怕哪处做的不好,便要贻害天下,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黎民。总而言之一句话:皇叔教我,皇叔帮我!只想刷个存在感的襄王殿下:???相识多年,怎么没发现二侄子还是块粘年糕呢!自从那日宴会之后,这小子除了日理万机之外,就频频召见他。各种问计,丁点也不拿他这个皇叔当外人。你不点明他装傻,你点明,他当场眼珠子就瞪圆:“这天下,侄儿就算谁也信不着,也不会信不着五叔啊!当初土木之变,孙氏都给您下懿旨了。但凡您有一丝丝野心,这江山也轮不到侄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