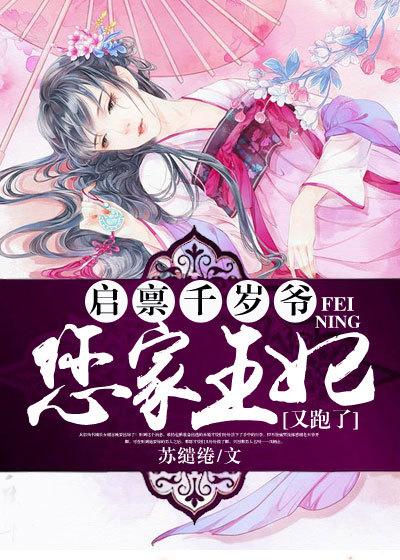02小说网>有罪 > 第224章(第1页)
第224章(第1页)
“没事。”刘珩摆摆手,“我认识很多我和沈醉的cp粉。丁寅你记得么?《流苏》的男三,他也是。”“我”梁策顿了顿,“我很喜欢《流苏》。”刘珩点了点头,目光似乎透过窗户看向远方。“那我就不问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了。”刘珩的语气变得幽静,“沈醉告诉我,你认识燕名扬。”梁策似有挣扎,还是嗯了一声。“你觉得他是个怎样的人。”刘珩问。梁策深吸了一口气,“我对他能做出的最好的评价,就是不作评价。”刘珩笑了,“你很诚实。”“人的感情很复杂。可在所有感情中,爱情又是最复杂的。”他端起柠檬水抿了口,“我很喜欢沈醉,我认为沈醉也喜欢我。但让你失望的是,我们之间并不是爱情。”梁策目光定定的,有些疑惑。“而燕名扬我很确信沈醉讨厌他。”刘珩话音沉稳,“不过,至少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沈醉与爱情有关的一切,都是寄托在他身上的。”与此同时,二楼。沈醉没有去洗手间。他走上了二楼,一个少有人去的地方。这里没有大灯,走廊灰暗一片。沈醉推开门,外面是个小阳台。他的目光在面前的停车场里迅速扫了一遍,很快便落在了左下方一辆停在树下的车上。那辆车亮起了车前灯,似乎是要离开的迹象。沈醉知道,那是燕名扬的车。此刻的燕名扬应该就坐在车里。不过,他大概率尚未看见站在二楼阳台上的沈醉。远方的天空在一片渐渐加深的蓝色中黑去,世界变得模糊。微热的晚风拂面,让人分不清是燥热还是凉爽。燕名扬的车稍稍向后倒了些,使车头方便开出来。沈醉双手抱臂,饶有兴致地观赏着。不一会儿,燕名扬的座驾驶离了这个停车场,在门口的马路上一拐,扬长而去。沈醉露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微笑。片刻后,他转身离开阳台,返回一楼。在两条街开外的一处闹中取静的高档别院里,燕名扬的客人已经等了很久。燕名扬手臂上挽着西装,脸上是标志性的微笑。他不紧不慢地等客人自己站起来,从桌前走到自己面前。桑栗栗这才接过了燕名扬的西装。“燕总。”客人走了过来。燕名扬脸上挂着的笑意如天色般渐深渐暗。他毫不讲长幼尊卑,主动朝对方伸出手,慢条斯理道,“谭总。”酷刑某种意义上来说,梁策的父亲谭总是燕名扬事业上的贵人。当年燕名扬即将毕业,初出茅庐。他之所以能将一大群同样成绩优异、才智过人的同学远远甩到身后,就是因为成为了谭总的秘书。对燕名扬来说,这是他的第一份正经工作,也是最后一份替别人打工的工作。燕名扬做什么事效率都很高——譬如学习、模仿、吸收资源等等。因此,这份工作他并没有干太久。但或许是多少念及旧恩,又或许是看在周立群的面子上,独立门户的燕名扬在羽翼渐丰后对谭总表面上还算尊敬,从前他总是恰到好处地保持着晚辈的礼节。直到,他今天主动伸出了手。谭总微微一怔,不算太意外。他握上了燕名扬的手,仿佛是早知道会有这一天,只有颊部肌肉上细密抖动着的皱纹昭示了他内心的波动。燕名扬并非善类,爬到旧主头上是迟早的事。可如果不是因为沈醉,或许他还会愿意多装一段时间。“好久不见。”燕名扬主动伸出手,又主动收了回去。他不再像从前一样请谭总坐主位,而是自己坐了上去,淡定而自然,“谭总今天找我,是为了梁策的事?”谭总年过半百,怎么也没想到儿子给自己作了个大死。他本想着让梁策跟在燕名扬手下,也算一种“传承”的纽带,说不定还能将利益关系维系得更久些。谁想到梁策不学习燕名扬的工作精神,反倒接手了他讳莫如深的前任。“小策被我惯坏了。”谭总皱着眉叹了口气,也坐了下来,“早知道他小的时候,我就该向老周学习,管得严一点儿。”“跟周达非相比,梁策还算好带。”燕名扬颇具亲和力地笑了笑,甚至主动给谭总倒了杯茶,“年轻人嘛,莽撞、幼稚、没经验都很正常,只要听话肯学就行。”“”谭总脑仁发疼。“我也没想到小策他”谭总接过茶后有些犹豫。他似乎想了想,放下茶杯直接道,“我明天就把他领回北京好好管教,绝不会再让他耽误沈醉老师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