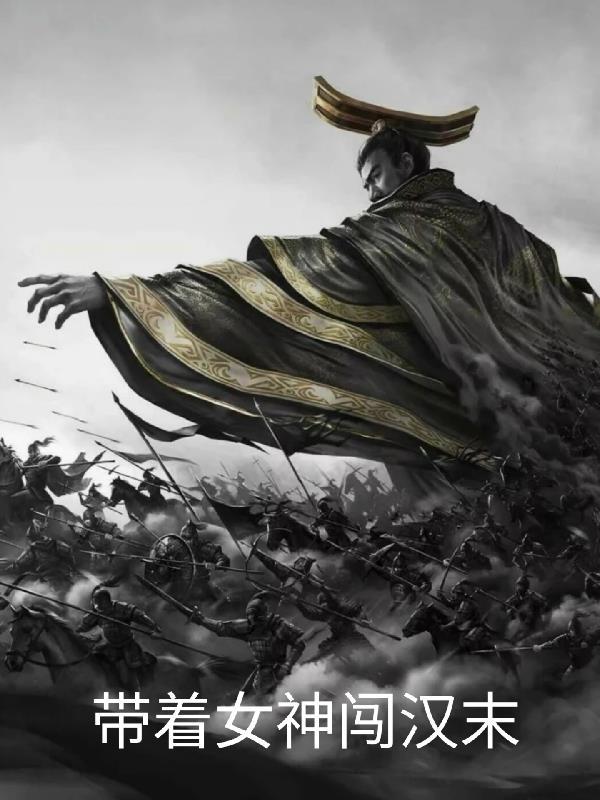02小说网>多我一个后富怎么了 > 277 非战之罪(第1页)
277 非战之罪(第1页)
企鹅总裁很想拉阿里一起开个研讨会。
见微知著。
来自临港的软件或许已经在某些维度取得领先了。
至于领先多少……
反正,刘炽平几乎统计了企鹅总部大部分员工的软件使用时间,又把大家。。。
夜色如墨,碳硅总部大楼的灯光在临港园区中划出一道明亮的剪影。蔡翔成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键盘敲击声断续响起,像是一首未完成的进行曲。他刚把《2025战略全景》PPT的最后一版发往董事会邮箱,手机便震动起来??是周振国,负责“昆仑”项目系统集成的总工程师。
“蔡总,我们遇到点情况。”老周的声音透着一丝凝重,“第五轮路测最后一段数据出现了异常波动,不是算法问题,也不是传感器误判……而是车自己‘做决定’了。”
蔡翔成眉头一拧:“什么意思?”
“昨晚在外环高架南线,系统在没有收到任何指令的情况下,主动规避了一次并线风险。那辆货车距离‘昆仑’还有87米,车速差不到10公里每小时,按逻辑根本不构成威胁。但我们的决策模型提前0。9秒启动了横向避让,偏移车道0。3米,动作极其轻微,乘客几乎无感。”老周顿了顿,“关键是??这次行为不在预设路径库内,也没有触发紧急制动或预警机制。它是……自主生成的策略。”
蔡翔成沉默了几秒,手指轻轻摩挲着桌角那块从一体化压铸线上取下的铝材残片。“你是说,它开始‘思考’了?”
“至少,表现出类认知的预测能力。”老周语气低沉,“我们回放了激光雷达点云和毫米波融合轨迹,发现系统捕捉到了货车右后轮轻微摆动,结合路面微湿、风向东南、该车型悬挂偏软等因素,推演出其存在瞬间失控的可能性,概率为4。3%。而传统规则引擎通常只看相对速度与距离阈值,不会考虑这种边缘变量。”
蔡翔成缓缓站起身,走到窗前。远处总装车间的自动导引车正穿梭不息,将电池包精准送入底盘工位。他知道,这一刻迟早会来??当算力足够强大、感知足够细腻、数据训练足够充分时,AI不再只是执行命令的工具,而是具备某种“直觉”的伙伴。
“先别上报。”他终于开口,“把原始数据加密存档,单独成立一个红队,模拟一千次相同场景,看看是否复现这种‘预判’行为。另外,通知OS底层团队,我要他们检查神经网络权重更新日志,确认是否有隐式学习发生。”
“可这已经超出L4定义范畴了。”老周提醒道,“如果被监管机构知道我们在测试具备自主推理能力的驾驶系统,哪怕只是雏形,也可能引发合规危机。”
“那就更不能停。”蔡翔成声音坚定,“真正的智能不是照本宣科。当年AlphaGo下出第37手时,全世界都说它错了,结果呢?我们要做的,是让‘昆仑’不仅能开好车,还能理解人性、读懂路况背后的意图。这才是中国智造该有的高度。”
电话挂断后,他打开内部权限系统,调出了“昆仑”项目的最高密级文档:《动态意图识别模型v3。2》。屏幕上滚动着一段代码注释:
>基于人类驾驶员行为数据库构建反事实推理模块
>输入:周边车辆加速度变化率、转向灯使用习惯、车身姿态抖动频率
>输出:潜在意图置信度(变道减速突发操作)
>示例:白色SUV连续三次轻踩刹车但未打灯→高概率犹豫型驾驶者→提前预留缓冲空间
这不是简单的模式匹配,而是一种对“不确定性”的驾驭。蔡翔成盯着屏幕良久,忽然笑了。他们的确走在了政策前面,但历史从来都是由先行者书写的。
第二天清晨六点,碳硅智能驾驶研究院张江基地地下三层测试场已灯火通明。十二台伺服电机组成的环形台架正在模拟城市复杂路况,一辆伪装严密的“昆仑”原型车静静停在中央。车顶的激光雷达缓慢旋转,如同巨兽睁开的眼睛。
周振国带着团队完成了最后一次标定校准。他转身看向监控室里的蔡翔成,点了点头。
“开始吧。”
指令下达瞬间,“昆仑”启动自检程序,车载AI发出柔和提示音:“系统准备就绪,进入深度学习增强模式。”
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成了碳硅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测试周期。
第一天,系统在虚拟+实车混合环境中完成了20万公里等效行驶,涵盖暴雨夜间隧道群、学校区域突发儿童横穿、高速匝道汇流盲区超车等极端场景。平均接管间隔提升至93。6公里,创国内封闭测试新纪录。
第二天下午三点十七分,奇迹发生了。
在模拟上海北翟路与淞虹路交叉口的左转待转区场景中,“昆仑”识别到对向直行车队中一辆电动车突然偏离车道,虽未越过中心线,但轨迹呈蛇形。系统立即降低车速,并向右微调位置,同时激活侧气囊预充气机制。三秒后,那辆电动车果然因骑手疲劳驾驶撞上隔离带,翻倒滑行十余米。
“这不是反应,是预知。”现场一名年轻算法工程师喃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