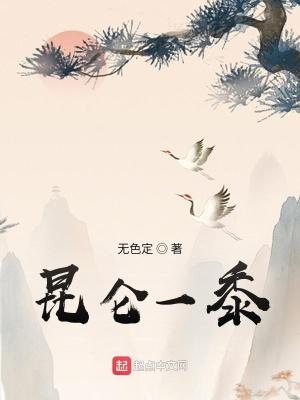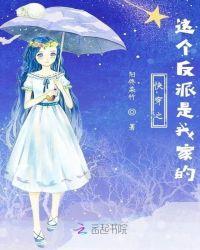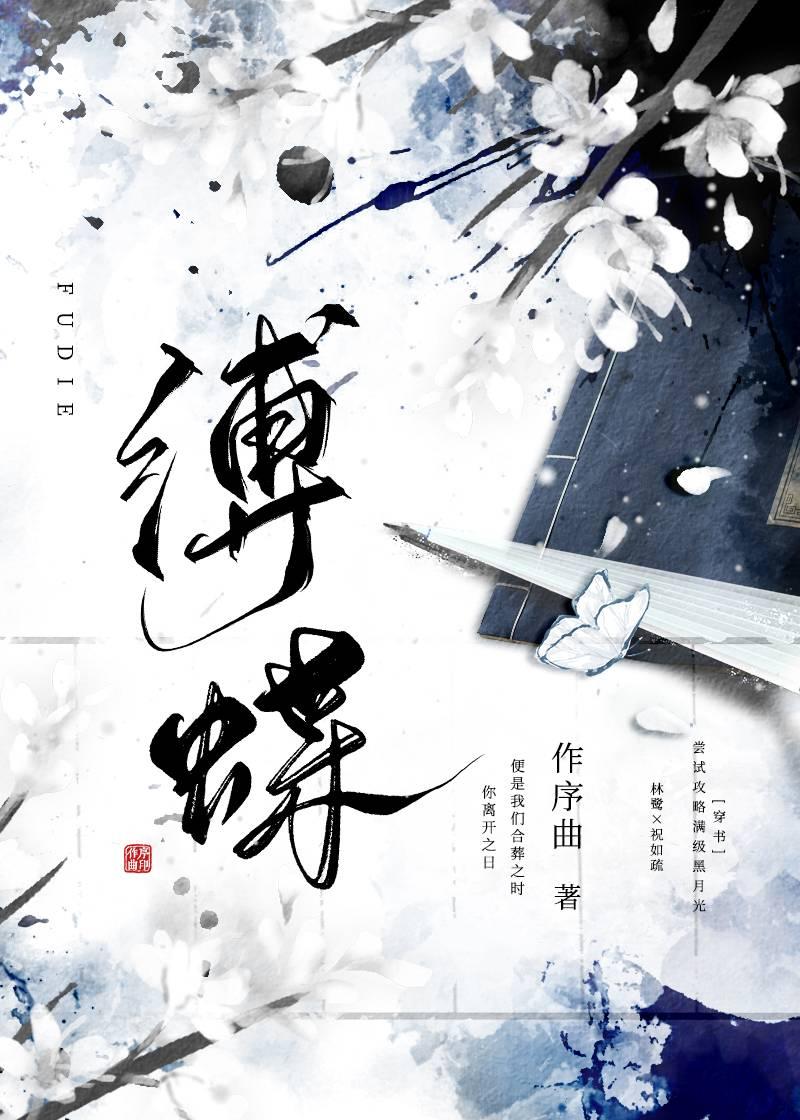02小说网>岁如皎月 > 第166章 作者有话说(第2页)
第166章 作者有话说(第2页)
赛前培训放在二楼,主要材是荷和睡莲,器有常用的六大器。
范梨所不知道的是,还有架构艺,还有选手带了立裁模特来,正在用红竹叶和珍珠钉大头针,一片片叶子摺叠顺著纹路往立裁模特身上固定造型。
这倒给宋欣欣提供了新的思路。
这位女选手钉的是一件旗袍样式,立领已经钉好了,半月袖也钉好了,开始做身体部分。
宋欣欣举起相机刚拍了两张照片,被选手发现了,以为她是来偷艺的,冲她吼了一句,“你干嘛呢?我的作品不许拍照。”
宋欣欣赶紧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
“你是参赛选手吗?”那女的喝问她。
这间屋子里有十几个人在做自己的作品,有六个是在做架构艺,其他的在插。
范梨在门口位置的一张桌上,选了一个宫廷篮正在插制,离宋欣欣那边只有三张桌子的距离,听到那女的大声,范梨见是宋欣欣惹了人家,慌忙过来拉住她,跟那女选手道歉,“对不起啊,她是我女儿,来给我拍照的,可能见你的作品有特色,就……对不住了。”
宋欣欣被拉到了门口,范梨压低嗓门教训她,“人家是参赛,你乱拍別人的东西,討骂得很。”
“不知者不为过,不敢了。”宋欣欣举手投降状。
晚上是理论课,传统插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莲英老师给选手们上课。
王莲英是传统插挖掘、整理和申遗的人,她是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八十二岁的她,从传统插的发展史讲到了现在如何秉持传统和歷史文化,將传统插很好地传承下去。她对中国传统插的推广和传承寄予了厚望。
听得范梨心潮澎湃,又得知主办方的张超老师,竟是王莲英的弟子,心中更是为自己庆幸,来得太值了。
翌日上午十点,初赛正式开始。
器是选手自己选,到范梨选的时候,只有一个比笔筒更大更高的天青色瓷筒,还选了一个斗笠碗,她构思的作品是笔筒插荷,碗里插睡莲,一高一矮中间用石头和苔蘚来连接。
范梨抽到四十號。
宋欣欣站在观眾位置举起相机捕捉范梨的动態,思考,剪枝,插,拿一枝荷安排位置,她还去折了一枝杨柳来,柳树在池塘边,荷在池塘里,將看到的景致艺术性地浓缩在方寸之间,很考验范梨的插技巧。
三十多公分高的大笔筒,需要用撒来固定材,而撒的做法,范梨在无锡刘若瓦的课堂上刚刚掌握了一点要领,仓促地在比赛中运用,范梨內心还是很惶恐的。
范梨用柳树枝和橡皮箍来做撒很耗时,九十分钟时间,也够她沉著应对了。
柳树的叶子压弯了柳枝,没有精神一样,范梨有想法子让它挺立起来,为了能稳住枝干,她將荷枝和苞一枝枝插在撒的空间中,按照她的构想,完成了基本的定位,柳枝的方向就是风的方向,范梨就將旁边的斗笠碗摆在筒的左侧,形成一个东风拂来的態势。
到了评奖环节,张老师和其他评委拿著本子对每个作品点评打分。
范梨看到评委们到自己的作品面前,心提起来了,和宋欣欣抓著手哆嗦。
“这个作品啊……在传统插中,是不需要用这些辅助的,石头和苔蘚多余了……大家看这两枝柳树枝,它与荷配得相得益彰,为什么呢?……像这个碗和这个筒高低大小的比例不平衡,但这位选手用几架將碗起高了,这样一看,就有意境了……”
老师点评选手作品时,正是最好学习的实际理论课,范梨跟在评委身边,不落下对每一个的评语,好的,不足的,要注意什么,她都听进去了,记住了。
所有选手都在二楼等待结果。
范梨见还剩了很多材,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环境不同,氛围不同,她有点如饥似渴地在练习。
宋欣欣的相机里都是她的动作和表情,脑海里一直盘旋著那位选手的立裁模特上的旗袍,想著回去后和叶小玉怎么来做一场服装与艺的视觉盛宴。
有老师来宣布进入决赛名单,有范梨。
“妈,妈,妈……恭喜你啊。”宋欣欣比范梨还激动。
“嗯,爭取拿一个奖。”范梨也激动得不行,却只敢和她悄悄地比了一个“加油”手势。
下午两点决赛,范梨抽到六號。
艺(插)大赛中的决赛命题,放在神秘箱里,什么主题什么材谁都不知道,很考验选手的现场发挥和经验积累。
每位选手都是两朵向日葵和三枝开的荷和三支苞,器是二十公分直径的斗笠碗,里面有个剑山。
范梨看到斗笠碗,窄底敞口的碗型,剑山不是很大,担心剑山的重量不够支撑粗杆的向日葵和荷。
她又想起,荷是水生植物,向日葵是陆生植物,虽说都是六月的材,但搭配在一起合適吗?
她偷瞥了眼左右两边的选手,她们有没有用向日葵。有的用了两枝,有的一枝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