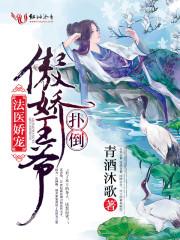02小说网>重生七零:开局打猎养家,我把妻女宠上天 > 579新商机(第1页)
579新商机(第1页)
赵振国想到此处,嘴角不自觉地漾出一抹笑意,扭头朝身旁的宋婉清问道:“媳妇儿,你觉着这物件儿用着得劲不?要是大家都能用上这好东西,你觉得咋样?”
宋婉清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问,先是微微一愣,眼神里闪过一丝疑惑,这东西从小本带回来的,大家都能用上,谈何容易啊,不过她紧接着就回过神来,明白了赵振国话里的意思。
“振国啊,听你这话头,莫不是打算做这买卖,把这生意给支棱起来?”
赵振国听媳妇这么一说,眼睛亮堂。。。。。。
巡演的第八站,他们来到了西南山区的一个彝族村落。这里山高林密,云雾缭绕,道路崎岖难行。晨曦和林强刚下车,就被扑面而来的湿冷空气打了个寒颤。
“这里的天气,真是阴晴不定。”晨曦裹紧了外套,看着远处若隐若现的山寨,“但这里的风景,真像一幅画。”
林强点头:“彝族人民世代生活在这片大山里,他们的生活节奏缓慢,却充满了诗意。”
社区负责人是一位姓阿木的中年男子,穿着彝族传统服饰,脸上带着高原特有的红晕。他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带他们参观了村里的文化广场。那是一座用石头砌成的空地,中央立着一根高高的图腾柱,四周挂着彝族的刺绣和乐器。
“我们这里的老人,年轻时种地、打猎、织布,现在年纪大了,腿脚不便,只能守着火塘过日子。”阿木叔说,“孩子们大多去了城里打工,一年难得回来一次。”
晨曦听后,轻声问:“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生活习惯?或者,有没有什么他们最熟悉的动作?”
阿木叔想了想:“彝族最熟悉的,是打鼓、跳舞、织布、烧火做饭,还有……跳火塘。”
晨曦眼中一亮:“那我们就从这些动作出发,编一支属于彝族的舞蹈。”
课程第一天,报名人数依旧寥寥。晨曦和林强没有气馁,而是带着志愿者们走进山寨,挨家挨户拜访。
他们来到一户人家,屋前挂着一串串辣椒,屋后是一片玉米地。一位姓吉克的老人坐在火塘边,手里拿着一根鼓槌。
“我年轻时,每天围着火塘跳舞,敲鼓,唱山歌。”吉克老人声音低沉,“现在腿疼得厉害,连站都站不稳了。”
晨曦蹲下身,轻声问:“您愿意和我跳一支舞吗?用您的鼓槌,跳一支属于您的舞。”
吉克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缓缓点头:“我试试。”
晨曦为他编了一支舞,名叫《火塘》。舞蹈动作简单,却充满象征意义:老人敲着鼓,仿佛在唤醒沉睡的记忆,孩子从远处走来,围坐在火塘边,两人相视一笑,紧紧相拥。
吉克老人跳完,眼角湿润:“原来,我还能跳。”
“您不只是跳得动,”晨曦轻声说,“您还在用舞步,告诉孩子,您这一生,从未停下。”
第二天,课程报名人数翻了一倍。第三天,整个文化广场都被挤满了。
晨曦和林强趁热打铁,开始组织小型汇报演出。他们鼓励老人们写下想对孩子说的话,再将这些话语编入舞蹈中,用动作表达出来。
“我以前觉得,我这一生就这样了。”一位姓阿依的阿姨在课堂上说,“孩子们都走了,我也老了,没什么可期待的。可你们来了,带着舞蹈,带着爱,让我重新找回了活着的意义。”
她的女儿在沿海城市打工,已经三年没回家。可当她跳完那支专门为母女设计的舞蹈《归火》后,女儿竟然主动打来了视频电话。
“妈,我看到你跳舞了。”女儿在电话里哽咽,“你跳得真好。”
阿依阿姨眼眶红了,却笑着点头:“你也要学,下次回家,我们一起跳。”
演出当天,晨曦和林强站在后台,看着台上那些原本沉默寡言的老人,如今牵着子女的手,跳着他们教的舞,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你看,”晨曦轻声说,“沉默也能被舞步打破。”
林强握住她的手:“是啊,只要有人愿意迈出第一步,爱就会重新流动。”
演出结束后,他们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信。写信的是一位独居老人,信纸有些泛黄,字迹略显颤抖:
“我一直以为,我这一生就这样了。孩子们都走了,我也老了,没什么可期待的。可你们来了,带着舞蹈,带着爱,让我重新找回了活着的意义。谢谢你们,让我知道,我还能跳,还能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