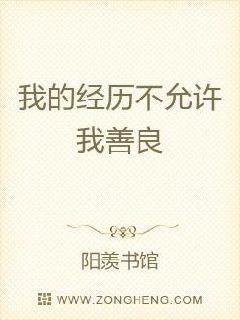02小说网>朝露待日晞 > 底牌(第2页)
底牌(第2页)
易康见了,停下正在整理书简的动作,双手捂住肚子笑得那叫一个合不拢嘴,“这可是左将军送来的九刀春酒,此酒称之为整个中原最烈的酒也不为过,你居然还敢在口干舌燥的时候把它当水喝。”
秦渊连忙又拎起茶壶往喉中灌入已经冰凉的茶水,缓和好一会儿才勉强能说话,只不过喉咙还火辣辣的,他剜了一眼还在幸灾乐祸的易康,“你怎么不早说?”
易康嬉笑摊手,“你也没问啊。”
最后一字收尾,陆旻放下笔,并未抬眸淡淡说道:“回来得挺快。”
秦渊随即恢复正经神色,打开包袱取出用竹简囊装着的卷宗呈上,“虽然我在家是没待几天,但是主上交待的事我都查探好了,韩逍的情况之前在信上就已经说了大概。这是灵帝时期关于宁望冤案的卷宗,这么久远的东西,翻找起来还真是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的时候落满了好厚一层灰,我已全都仔细擦拭干净。”
陆旻听罢,落在卷宗上的视线悠然抬起,“辛苦你了。”
秦渊抬手摸摸后脑勺,“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他怎么觉得,大将军突如其来的夸赞,容易让人脊背发凉……
“当年这起案件是由你祖父审理的?”陆旻问。
秦渊答道:“是,父亲说,宁望是个惩恶扬善的好人,当年祖君因误判此案致使宁望落下了一身伤病还失去左臂,因而心存愧疚赠予对方一把秦氏的祖传匕首,宁望亦或是他的后人可凭借那把匕首要求秦氏为宁氏做一件事,承诺永远作数。”
陆旻挑了挑眉,唇角噙着浅笑,“无论何事?”
秦渊思量一会,确定道:“对,无论何事。但自从祖君逝世后,我们秦氏就没再有过宁氏的消息。”
说着说着,他又突然发觉一丝诡异,宁氏,宁,宁……能让主上关心的姓宁的人还能有谁,可不就只有那宁予安吗?!!
秦渊轻捶手背,恍然大悟道:“主上是不是早就怀疑宁予安就是宁望的后人?”
陆旻未置可否,眼神中就已经蕴含了一切。
秦渊在脑海中比对起宁望儿子以及宁予安祖父姓名,瞬间意下了然,脸也皱起苦恼呢喃道:“没想到我们秦氏竟然还欠着宁予安的债。”
陆旻轻轻摇头失笑,语气意味不明,“你此番查探出来的极渊海盗之首名讳很明显只是个代称,不是真名。而几十年前创建谲风岛之人,亦是左臂残缺。”
话语意思再清楚不过。
震惊已经盖住了嗓子的不舒服,秦渊呵叹讥嘲,“怪不得他可以招降极渊海盗呢,原来就是让自家小喽啰投降。”
易康听了也忍不住惊呼,“这位御史中丞身上的秘密,还真是一个比一个刺激。”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着。
陆旻深幽的目光落回至手中卷宗,又多了几分沉然。
岭西秦氏。
原来这就是你的底牌么?
-
“阿嚏——”
宁予安抬手搓了搓鼻子,拢紧身上披风,她这身体有个很奇怪的特点,在凶险环境下,纵然身着单衣处于数九寒天都没有知觉,可一旦稍微安逸下来,就会十分畏寒。
当然,打喷嚏这事,也说不准是不是有人在背后蛐蛐她。
门外传来侍卫通报声,“启禀御史中丞,刘县令求见。”
宁予安嘴角微勾,将手中把玩着的笔随手搁置在一旁,“让他进来。”
刘嵩快步入内,也夹带入了不少暗夜寒气,他双手举着供词一揖,“经过下官重刑审问,那张沿终于还是张嘴吐出了真相,此为审讯供词,请御史中丞过目。”
宁予安莞尔一笑,“既如此,拿过来吧。”
刘嵩将供词递上,并同时悄悄打量着宁予安的神色,见其笑意一点点收起,面容归于平静,他内心也跟着忐忑起来,小心翼翼问道:“中丞有何疑问?”
宁予安啧叹摇头,很是为难道:“刘县令可知,廷尉大人,是二殿下的岳丈,也即将成为太子殿下的岳丈。”
他怎么就忘了,陛下已经在除夕夜给太子殿下与廷尉幼女赐婚的事,而御史中丞又是站在太子殿下那一方的。
“要不,”刘嵩脑子飞速转动着,慌乱道:“要不下官再去审问一番,廷尉大人怎么可能做出构陷抚军将军的事,一定是哪里出了误会,那张沿简直是厚颜无耻,血口喷人,先后诋毁两名朝廷命官,实在是可恨,可恨至极……”
宁予安抬手揉额,闭了闭眼说道:“刘县令不必如此义愤填膺,遇事心平气和方有助长寿。”
刘嵩面露尴尬,俄顷后声音放低了些,“那中丞以为,接下来该如何?”
宁予安笑道:“就依刘县令所言,继续严加审问,同时查探丢失的那笔赈灾银去处,还有,也是最重要的一件,派人去看看张主簿的家人是否安好,以免被别有用心之人掳了去。”
“记住,后面这件事,需不动声色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