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小说网>和疯批反派HE了 > 第209章(第1页)
第209章(第1页)
兴庆宫的书房,不仅有她带去为他解闷的物件,也有他为功课不济的她标注好的勾画圈点,耐心讲解的日日夜夜。
「君为国出质,臣亦感佩君之高义,不计颠沛动荡丶同进同退丶生死与共,创飞廉丶谋归国丶举大计丶匡正统。聆君之教诲,受君之导引,始见天地高远丶众生万千,初悟治国平天下之道。」
起云楼的铮铮誓言,最初的飞廉七星,灵昌宫变互相托付的后背,三江村闲话史书背后的斑斑血泪,大庆门上万众山呼丶众星拱辰。
「臣出身低下,承君之厚爱抬举,使臣苟以微芥之身,荣登殿堂,祀圣祖之宗庙,持六宫之中馈。」
她视他如至高至明之日月,敬而重之丶远之,他固执地将她扶上尊位,与他一并钉在王座之上丶俯瞰这巍峨河山。虽让她心力交瘁,却也有幸站在更高的角度,重新思考何为家国丶何为天下丶何为苍生。
「盖闻夫妇之礼,是宿世之因,幽怀合卺之欢,欢念同牢之乐。今已不和,乃是结缡初衷之谬错。君以臣为妻,皆因南园之遗爱丶故剑之情深;臣以君为夫,俱由济弱之慈念丶扶倾之壮志。失之毫厘,终南辕而北辙。」
成婚之后,她将那抹悸动的红丶永远锁在不见光的角落,断情绝爱。把全副身心献与大翊,外辅国政丶执掌中馈丶开枝散叶,待他敬重丶乖顺丶温婉丶关怀,像君父丶像袍泽丶像挚友丶像亲人,却唯独不像夫婿。
全然不顾他想要的,是那个曾对他毫无保留丶与他心有灵犀的阿七。因为给不了,所以只有忘记丶只有忽略。
「两自不和,反目生嫌,无秦晋之同欢,有参商之别恨,六亲聚而成怨,九族见而含恨。」
他只想要一个阿七,可她早不是那个满心满眼只有他的阿七。他却仍习惯地不去了解她所思所想,性子又内敛端肃,所以他们从不曾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丶将话说开。
于是,他执拗地认为,他们之间所有问题的根源,是苻洵出现丶她移情别恋。
于是,本就敏感多疑的他,最终被重重心事逼得癫狂,先不顾形势丶执拗着虚置六宫,又将才不配位的褚氏阖族抬入中枢,她和褚氏全族皆被架上火堆,除了牢牢依附于他,孤立无援丶无路可退丶无处可去。
「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遂会及诸亲,各还本道。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和离书的下方空白处,「褚舜英」三个字旁边,深红的龙泉泥盖着元璟的钤印。
盖上钤印之前,元璟意味深长看着她说:「生死虽是大事,却也有一桩好处,你们不必再勉强维持举案齐眉,可以跳出原来的身份拘束,重新想想自己要走什么路。」
「自后,夫则任娶贤妻,同牢延不死之龙,合卺契长生之奉。伏愿郎君千秋万岁。褚舜英谨于延光五年六月初二立。」
舜英举起酒杯,与对面轻轻碰杯,一饮而尽:「这一杯,给死在冰冷王座的山上雪丶云中月。」
第二杯,对着东南遥遥一敬,一饮而尽:「这一杯,给死在宁皋山丶丹河谷丶龙兴楼丶笠泽大营和龙川湖的阿七。」
第三杯,对着升阳和武原城的方向敬了敬,舒臂丶浇洒在地:「这一杯,给困死在婚姻囚笼的永平王与褚王后。」
「我与阿洵之间不能隔着人命,所以,你可要好好活着。」
她慢慢站起身,将丝缎和酒壶酒杯留在原地,收拾好地毡和刀,面向梨林深处丶端端正正躬身长揖,一字一字扬声高呼:「褚舜英拜别大翊永平王陛下。」
「这一次,不是商议,是告知。」
期待过丶失望过丶爱过丶恨过……所有情分已消磨殆尽,终究要互相放过。
。
荣都奉宁,又是桂香飘飞满城时。
飞花楼丶醉花春包间,苻洵穿了一身海棠红雨丝锦,心不在焉看着台上歌舞。
揭开黑陶酒坛的泥封,清甜米酒带着甘醇微苦的桂花香。他小心翼翼双手托起坛身,将酒倒入敞口杯,倒得很慢丶害怕弄洒哪怕一滴。
这是第五坛她亲手酿的桂花酒。
二十九坛桂花酿,去年生辰喝掉三坛,今年五月初十喝掉一坛。
喝一坛少一坛,苻洵情不自禁放缓速度,喝得更慢丶更加仔细。
「我就说怎么从宫宴上早早溜走,敢情是跑这来喝好酒了」,帘幕拂动,沁人心脾的水泽草木香气越来越近,一袭淡蓝长袍在他对面坐下,「建业侯好雅兴。」
「平南侯不是来探视王后的吗,怎么老盯着我?」苻洵挑了挑眉,「这酒,没你的份。」
元旭不以为意地笑了笑:「懂——尊夫人善酿酒,侯爷是来这儿睹物思人了。」
哪壶不开提哪壶,姓元的都是黑心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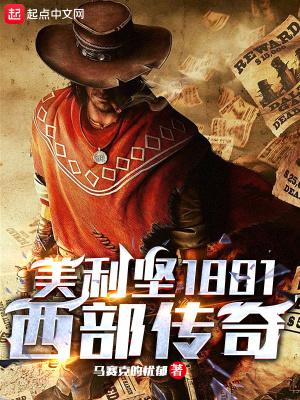

![女主一心搞钱[八零]](/img/819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