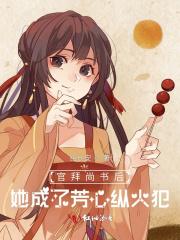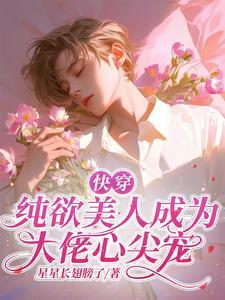02小说网>清枝 > 7075(第13页)
7075(第13页)
一回来又径直去了书房,每日待处理的公文在案头堆得老高,书房的烛火总要燃到深夜才熄灭。
清枝这边被婚礼的琐事缠得脱不开身,光是核对礼单,试穿吉服就得耗去大半天的功夫,还得趁着夜深人静时,就着一盏烛火翻看医书。
莫大夫给徐闻铮新配了药,特意叮嘱说他这身子还得细细温养,半点马虎不得。
清枝每日晨起总要悄悄问过小厮,听说徐闻铮夜里没咳,睡得也安稳,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这日清枝收到了林升月的帖子,说是两月未见,想约她小聚。清枝正巧想带她看看自己的新铺子,便将地点定在了清晏楼。
谁知到了地方,不仅林升月在,连林照月和孟清澜也来了。
清枝引着她们往后院去,那里有一处她特意用青竹搭建的小亭子。
小亭子四面都垂着素纱幔帐,竹帘半卷时,既能透进丝丝凉风,又叫人瞧不真切里头得情形。
更特别的是,清枝还命人将院中的溪流引了一条分支流过小亭中央,水声淙淙,将暑气都冲散了七八分。
林升月在韶州城待久了,性子也洒脱了不少。一见这溪水清亮,当即脱了绣鞋,褪去罗袜,赤着脚就往水里一放。
她眯着眼叹道,“真痛快!”脚丫子在水里不停地踩着水花。
清枝端着青瓷盘进来,金黄的炸荷酥还冒着热气。
“知道你馋这个。”她笑着将盘子往林升月面前一推,“刚出锅的,小心烫。”
林升月眼睛一亮,迫不及待地拈起一块就往嘴里送。
“可算盼到了!”她含糊不清地说着,酥脆的声响从唇齿间漏了出来,“府里的厨娘试了多少回,总差那么点意思。”
清枝刚在石凳上落座,林升月就忙着介绍,“这位是孟姐姐,孟清澜,京都第一才女,琴棋书画没有她不精的。”
说着她又指了指身旁,“我堂姐林昭月,你们上回在别院的荷宴上见过的,也是个大才女。”
清枝略一低头,唇角轻扬,朝二人浅浅一笑。那两人亦不约而同地颔首回礼,目光交汇间竟有几分默契。
林照月轻摇团扇,温声说道,“升月先前同我说你要在京都开酒楼,我只当是姑娘家的玩笑话。”
她顿了顿,眼底带着几分钦佩,“没成想,你竟真做成了。”
“何止做成了,如今这清晏楼在京都可是颇负盛名的。”林升月捏着半块炸荷酥,得意地扬起下巴,“她可是京都城里独一份的女东家。”
清枝执壶为众人添茶,闻言只是浅笑,“这第一人总得有人来做。今日我蹚了这条路,待往后再有姊妹们当东家,世人也就见怪不怪了。”
孟清澜手中的茶盏顿在半空,她抬眸深深看了清枝一眼。
清枝恰在这时抬头,四目相对间,她朝孟清澜莞尔一笑,眼尾弯成了月牙。
近来京都各个坊间,除了孟清澜的传闻,就数清枝最惹人议论。
一个流放归来的女子,竟能攀上侯府这门亲事,任谁听了都要酸上两句。
孟清澜今日一瞧,见眼前这姑娘似乎并不在意,照旧开着她的酒楼,备着她的婚事,听林升月说她还抽空研习医术,该做什么做什么,那些闲话似乎连她的衣角都沾不上。
孟清澜暗自打量,清枝看她的眼神澄澈得很,既无旁人那种刺探的意味,也不刻意亲近,就像对待寻常的新友,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这些日子,多少旧交借着探望之名来孟府,明里暗里都要打听太子暴毙当日的情形,还有这些年她的境遇。
那些人眼里藏不住的,有猎奇,有怜悯,也有等着看她落魄的窃喜。
而清枝的眼里,竟然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
孟清澜素来不是个热络性子,能入她眼的人本就不多,平日里往来的,也多是场面上的客套。
可奇怪的是,眼前这姑娘才说了几句话,她心里就莫名生出几分亲近来,连她自己都觉得诧异。
那句“这第一人总得有人来做”在她心头盘旋不去。
分明是句再朴实不过的话语,却像一颗石子,在她沉寂已久的心湖里,激起了层层涟漪。
蝉鸣渐歇的黄昏,四人踏出清晏楼时,西边的天空正绽放着橘红的晚霞,晚风裹着未消的暑气,掠过面颊时,仍带着白日的余温。
停在巷口榆树下的马车忽地动了动,随即就看见徐闻铮单手撩着车帘,身形利落地一跃而下。
他身着月白夏袍,衣料轻薄,被晚风一吹便勾勒出挺拔的身形,时而贴住腰线,时而掠过肩背,将那一副宽肩窄腰的好身量勾勒得若隐若现。
他朝清枝走去,步子从容,自有一股风流的气度。
走近时,徐闻铮与那三位官家小姐略一颔首,三位姑娘齐齐福身,算作回礼。
![钓系美人成为炮灰攻后[快穿]](/img/631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