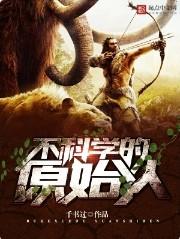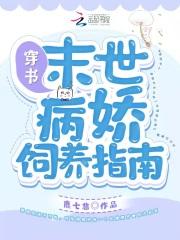02小说网>宿敌登基为帝之后 > 90100(第22页)
90100(第22页)
顾宁熙详细观察着田中犁具的使用状况,在农人们闲暇时,与他们攀谈,想再加以改进。
知晓她是京中派来的钦差,百姓们热络无比,七嘴八舌地与她说着田地、庄稼,还有今年可能的收成
朝廷赋税一降再降,便是大字不识的百姓都知道,本朝与前朝不一样了。不再有服不完的力役,交不完的杂税。
百姓对朝廷的态度,单看他们对钦使便可知。
顾宁熙踩在松软泥土间,惯来立于朝堂金砖的、洁净的官靴糊满了淤泥。
可这是脚踏实地的感受,是在京都永远都不会有的体悟。
述职的公文写了一页又一页,闲暇时分顾宁熙也会去信回京,与朝堂上的那人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
他在外征战时,大约见惯了百姓流离失所的场景罢,知晓仁政永远会比所谓的严刑更能安定人心。战火频仍,他以数年的时间平定了中原,结束无休无止的战乱,怎可能不得人心呢?
夏日炎炎,禾苗碧绿,仿佛要透过灼热的风给人带来清凉。
顾宁熙抱膝坐于柳树荫下,她自幼生于钟鸣鼎食之家,从读书到科举入仕,安逸顺遂。
她从前想着外放造福一方百姓,可她从不曾到田间地头,真正看过民生疾苦。有些政局上的设想,就如空中楼阁一般,天真、虚妄。
第97章避子汤
天观元年八月,耗时半年,户部正式完成了详尽的全国人口清查。
大晋三百零三州,共有百姓四百二十余万户,尚不及前代鼎盛时期的一半。
连年战乱,中原人口锐减。突厥在北仍虎视眈眈,边患未平,国耻未雪。
除过劝课农桑,发展生产,朝廷接连下诏,鼓励百姓生育,增添人口,充实劳力。
五月时节,南地新到的贡果送进了昭王府。
头一茬的杨梅饱满多汁,酸甜相宜。紫红晶莹的颜色,圆滚滚盛在碧玉盘中,那叫一个新鲜可口。石榴也好,一粒粒石榴籽艳如红宝石。再有新贡的枇杷,五月里就数这些果子最俏,连后宫中都还少见,只先送了皇后娘娘宫里。
陆憬合了奏案,尚未开口问询,孙敬已会意道:“回禀殿下,顾大人午前告了半日假,眼下不在王府中。”
“告假?”陆憬微不可察地蹙了蹙眉,“可是病了?”
孙敬笑着道:“顾大人说是有私事,午后便回王府点卯。”
殿下惯来通情达理,顾大人又是难得一回告假,昭王府内专司此事的林大人当然也没有不允的道理。
王府内的大人们当值与否本与孙敬无关,但既然是顾大人,他难免多留意些。
“好。”
殿下果然没有多说什么,孙敬吩咐侍女端了新鲜的果子来。他瞧顾大人与殿下是少年相识的玩伴,长大后彼此难免生疏些。没成想等殿下从战场归来,他们二人反而又亲近许多。
孙敬笑着感慨,近来殿下也是时常召顾大人入见。
一轮红日挂于天幕,巳时的天气还不算炎热。记着母亲的叮嘱,顾宁熙黄昏散值得早,便去给长辈们请安。
到了萱和院前,却被仆妇拦下。回东宫的日子比顾宁熙想象得还要安顺些。
如她所愿,她既在昭王府中许久,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太子殿下都不会放心再重用她。
东宫人才济济,少她一个六品官也无妨。
顾宁熙心中轻松,趁着表兄还在京城,挑了个闲暇的散值日子邀他到茶楼一聚。
茶香氤氲,孟庭瞧眉宇间蕴着欢喜神色的人,也不自觉随她浅笑:“这几日瞧你心情不错。”
“是啊。”顾宁熙为表兄斟茶,今日设宴,一来是为答谢表兄替她做了那把短弩,二来则是小小地庆贺她从昭王府全身而退。
她与昭王殿下的关系修复得不错,对东宫也是一向恭谨。日后无论是谁登基,她应当都可以顺利请旨外放。
等她改进完手中的江东犁,再琢磨新筒车的搭建,三不五时参与几项休憩工事。攒足了政绩,外放时应当能有更多选择余地。
孟庭瞧她面上的明媚笑意:“不过之前还听你说,你在昭王府中过得尚可?”
如今离了王府,熙儿如此开怀,难不成是在王府中受了委屈?
“这个倒是不曾。”
顾宁熙喝了口茶,其实她在留在昭王府中也可。只不过她毕竟是东宫的人,长久留在昭王府不便。况且昭王殿下虽然眼下没有怀疑她的身份,但天长日久,难免一不小心惹他察觉。时机既恰当,她及时抽身离开更好。
她思虑周全,孟庭含笑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