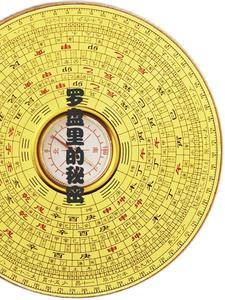02小说网>直播共享阴阳眼后[玄学] > 5060(第6页)
5060(第6页)
车子驶出市区,阳光正好,但梁红宁的心却沉甸甸的,越靠近目的地,那股如影随形,被什么东西死死盯着的寒意又隐隐浮现,让她坐立不安。
司机也嘀咕了一句:“没开空调啊,怎么这么冷。”
梁红宁的脸又白了,这时姜楚绪开口了:“没事,安心。”
或许是姜楚绪的话有什么魔力,梁红宁放松下来。
车子停在村口,付钱下车,上午的村庄比夜晚多了几分生气,但陈婆那栋位于村子边缘的老屋依旧显得孤零零的,透着一股沉寂。
“你先去问问陈婆的事情。”姜楚绪道。
梁红宁不清楚陈婆的太多事情,但是村里的其他老人或许知道。
梁红宁强压着心悸,走向村口一棵大树下坐着闲聊的几位老人。
“王爷爷,李奶奶,”梁红宁认得其中两位,“您俩这两天看见陈婆了吗?我找她好几回,门都锁着。”
被称作王爷爷的老人放下手里的旱烟杆,叹了口气。
“是红宁啊,昨儿个晌午还听见她那屋里有动静,乒乒乓乓的,像在摔东西,我问了一嘴,她说没事,不小心摔了个碗,应该是没啥事。”
旁边的李奶奶压低声音,带着点忌讳:“红宁啊,陈婆问米是灵,可那是早年风光!她眼睛怎么瞎的,你晓得不?
就是年轻时一次问米,请来了不该请的凶东西!斗法斗不过,伤了眼睛,也伤了根本,这些年找她的人少了,都说她请来的东西越来越‘凶’,越来越难送走,你找她干啥?唉……”
老人们的话印证了姜楚绪的推测,也让梁红宁的心沉到了谷底。
她谢过老人,更加焦急地奔向陈婆的老屋。
越靠近那栋房子,那股被死死盯着的毛骨悚然感就越发强烈,连上午的阳光都驱不散这股寒意。
院门紧闭着,是从里面闩上的
这更反常了,陈婆眼睛看不见,平时很少从里面闩门。
“陈婆,陈婆您在家吗?开门啊,是我,红宁!”梁红宁用力拍门,声音在安静的上午格外清晰。
里面死一般寂静。
恐惧和焦急撕扯着她,梁红宁退后几步,看着那扇门,一咬牙,用尽全身力气猛地撞了上去。
“砰,砰,砰!”
连续撞击了几次,木门被她硬生生撞开。
镜头剧烈晃动,扫向屋内。
上午的阳光从敞开的门和窗户斜射进来,照亮了飞舞的尘埃。
堂屋里一片狼藉,供桌上的烛台倒了,蜡油凝固,香炉翻扣在地,香灰洒得到处都是。
而最触目惊心的是地上铺满了大片大片焦黑的米粒。
“陈婆!陈婆!”梁红宁的声音带着哭腔,举着手机,她颤抖着走过每个角落。
堂屋,空的。
卧室,空的。
厨房,空的。
陈婆踪影全无,而且看屋里的样子,陈婆已经离开很久了,柜子里的饭菜都馊了,陈婆绝对不会允许自己活成这样。
“不在,她真的不在家。”梁红宁的心沉到了冰点,巨大的恐慌和无助让她靠在门框上。
“主播,陈婆不见了!地上全是黑米。”
梁红宁好歹也是问过几次,自然直到如果米变成黑的,说明不太好,可能是阴祟邪气太多。
就在这时,一个模糊的记忆猛地浮现。
那是陈婆精神尚好时,某次闲聊,老人家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红宁啊,我这把老骨头,哪天要是真不行了,你就别费劲找我了,后山西边那棵老槐树旁边,我给自己留了个坑,棺材都备下了,老婆子我孤家寡人,到时候自己爬进去,落个清静。”
当时梁红宁只当是老人家的怪话,此时她却觉得陈婆或许在那儿。
“后山老槐树。”梁红宁喃喃自语,她不再犹豫,转身冲出老屋,朝着村子后山的方向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