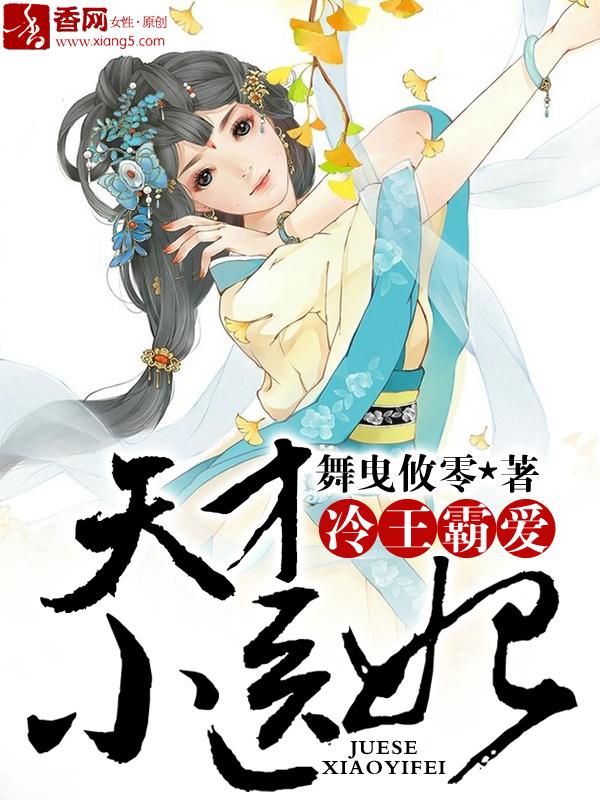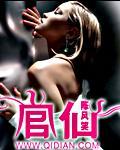02小说网>年代:巨额私房钱被媳妇儿发现了 > 第430章 泊林电影的邀请函大戏正式开场(第2页)
第430章 泊林电影的邀请函大戏正式开场(第2页)
艺术创作也一样,不用非要剑拔弩张。”他顿了顿,话锋一转,“这次文代会上的风波,你别往心里去。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才是改革该有的样子。”
程学民点点头:“我明白的!”
“其实安绍康他们的批评,也不是全无道理。通俗文学确实要警惕低俗化,这个度得把握好。”
“你能这么想就好!“廖老拿起桌上的《高山下的环》手稿,封面上已经批满了红色的修改意见,“你在前线的那段经历,写进书里了?”
“写了一小段,怕太敏感,没敢多写。“程学民有些不好意思,“当时在猫耳洞待了七天,听战士们讲了很多故事,比我编的精彩多了。”
廖老的目光沉了沉,点头称赞道:“该写的就得写!老百姓不光需要娱乐,也需要知道,安宁的日子是怎么来的。”
他又指着窗外的松树,说道:“你看那树,冬天看着光秃秃的,春天一到,照样发芽。好作品也一样,经得起风雪。”
午餐很简单,四菜一汤,都是家常口味。
廖老特意让厨师加了道陕北的糜子饭,笑着说:“让你尝尝家乡的味道。”
程学民非常的触动,觉得这顿饭虽然没有他想象中的奢华,但廖老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让他这顿饭吃的很轻松,倍感荣幸。
临走时,廖老握着他的手,说道:“还是那句话,不用有压力,能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变化,就够了。”
程学民望着老人鬓角的白发,突然想起冯父常说的话:“真正的大人物,都像老黄牛,默默做事,不声张。”
回到人民大礼堂时,午休已经结束。
程学民刚走进会场,就被燕影厂的人围了起来,询问着他在海子里用餐的殊荣。
程学民的目光扫过会场,看见江城大学的席位空荡荡的,只有几张折迭椅孤零零地靠在墙上。
老厂长汪杨在他耳边,偷偷的嘀咕了一句:“刚才李默安被抬走了,听说。吐了血。”
“人没事吧?”程学民皱了皱眉。
“医生说情绪激动引发的胃出血,问题不大。“老厂长叹了口气,说道,“也是个可怜人,太钻牛角尖了。“
程学民没说话,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坐下。
主席台上,茅老正在发言,讲的是“文学的包容性”。
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他白的头发上,像镀了层金。程学民突然想起廖老的话,“允许不同声音存在“,心里豁然开朗。
散会时,他在门口遇见了安绍康。
年轻人眼眶通红,手里捏着个牛皮纸信封,看见程学民就躲开了,却又在几步外停下,转身走回来,把信封递过来:“这是。李老师让我交给您的。“
信封里是几篇文章的剪报,正是抨击程学民的那些,上面用红笔改得密密麻麻,最后一句是:“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程学民抬头时,安绍康已经走远了,背影在夕阳里拉得很长,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汪厂长凑过来看了看剪报,笑道:“这老李,总算认账了。”
程学民却把剪报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他知道,这些文字或许尖锐,却也提醒着他,永远别丢掉对文学的敬畏。
夜色渐浓时,程学民跟丈母娘老丈人一起骑着自行车穿过胡同,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透出暖黄的灯光,夹杂着饭菜的香气和收音机里的评书声。
不禁让程学民想起《太极》里的最后一个镜头:宗师站在山顶,看着朝阳穿透云层,缓缓打出第一式。
或许,真正的太极,不是打倒对手,而是理解对手。
真正的改革,不是消灭异见,而是在不同声音里,找到前进的方向。
程学民蹬着自行车,车轮碾过积雪的声音,像首轻快的歌,在寂静的胡同里远远传开。
“学民,你慢着一点!”
后面追逐的冯父冯母心里的石头,也算是重重的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