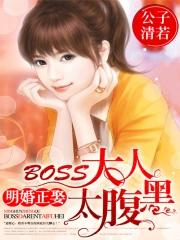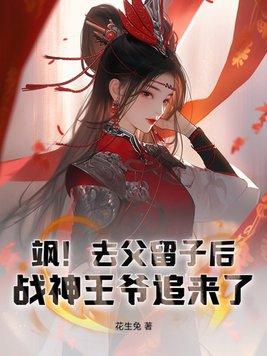02小说网>为变法,我视死如归 > 第237章 王小仙的底色到底还是个好人啊(第1页)
第237章 王小仙的底色到底还是个好人啊(第1页)
兴庆府,用黄河泥沙混合糯米浆夯筑的土城,此刻却在西斜的日头下显出几分斑驳,城门口的两尊石狮子,爪下原本刻着的“震慑汉疆”四字,如今已经被彻底磨去,换上了“为宋护边”这四个莫名其妙的新刻之字。
穿。。。
秋去冬来,统万城的天空再次被铅灰色云层笼罩。北岭渠畔的柳树早已落尽黄叶,唯有渠水汩汩流淌,映着霜雪微光,如一条银蛇蜿蜒于荒原之间。王小仙立于渠首石台之上,手中拄着一根乌木杖,身形清瘦,双颊凹陷,唇色泛青,却仍挺直脊背,目光沉静地扫过远处正在夯土筑坝的民工队伍。
三日前,他咳出的血已不再是点点猩红,而是成口黑紫,连郎中也不敢再称“尚可调养”,只跪地流泪道:“大人五脏俱损,若不卧床静休,怕是撑不过这个年关。”他却只是摆手,命人将药罐倒进火盆烧了,说:“新政刚稳,我不能倒。一倒,便是万劫不复。”
此刻,苏辙悄然走近,递上一碗热姜汤。“哥儿,喝一口吧,风大。”
王小仙接过,浅啜一口,苦涩入喉,却暖不了心肺。他望着远处工地公告栏上张贴的《阳光账册》,新一期的支出明细刚刚更新:水泥三百车、铁锹五百柄、粮米八百石……每一笔皆有签押与印鉴,百姓围在栏前指指点点,有人点头称善,也有人皱眉质疑。巡检司的小吏在一旁耐心解释,竟无一人喧哗。
“这才叫治世。”王小仙轻声道,“不是官说了算,是理说了算。”
苏辙低叹:“可京中又有动静了。昨日快马送来密报,御史台虽收回弹章,但旧党并未罢休。韩维大人再度致信,言宫中已有‘调虎离山’之议??欲以嘉奖为名,召你入京受勋,实则夺权架空。”
王小仙冷笑:“他们怕的从来不是我贪赃枉法,而是我让百姓学会了问‘凭什么’。”
他顿了顿,缓缓道:“我若不去,是抗旨;我去,则新政必崩。唯一的路,是我留在这里,哪怕只剩一口气。”
话音未落,阿勒坦疾步奔来,脸上带着少有的惊色:“先生!夏州急报??昨夜子时,文庙遭焚!”
王小仙猛然转身,木杖重重顿地:“什么?!”
“火起于后殿藏书阁,烧毁了半座讲堂,《咨议录》原本尽毁,所幸守夜学童及时发现,扑救得快,未及蔓延至正殿。”阿勒坦喘息道,“现场留有一封血书,写着‘妖言惑众,天理难容’八字,署名‘忠义士’。”
苏辙脸色骤变:“这是冲着《河朔新政实录》来的!他们知道那本书不只是记录,更是种子??种在年轻人心里的规矩意识!”
王小仙沉默良久,忽然仰天一笑,笑声凄厉如裂帛:“烧得好啊!烧一本书,就能吓退万人之心么?我早该想到,他们不敢明杀我,便要毁我的道统!”
他猛地转身,对阿勒坦下令:“传令下去,三日内重修文庙,材料不限,工期不限,务必比原先高一丈、阔三尺!同时,召集全境所有蕃汉学堂教习、学生代表、乡老士绅,在废墟前召开‘焚庙问心大会’??我要让天下人看看,火能烧纸,烧不了人心!”
三日后,寒风刺骨,文庙残垣断壁前搭起一座露天高台。焦木未清,瓦砾遍地,却已有数千人自各州县赶来,手持蜡烛,肃然而立。妇女抱着孩子,老人拄着拐杖,少年捧着抄本,连西域商队也遣使列席。火光照亮每一张脸,映出愤怒、悲痛,更有倔强。
王小仙披着旧紫袍走上台,未戴官帽,发髻散乱,面色苍白如纸,声音却如洪钟震耳:“昨夜一把火,烧的是屋宇,照的却是人心!是谁怕我们读书?是谁怕我们议事?是谁怕百姓识字之后,不再跪着听命,而是站起来问一句‘这税,合不合理’?!”
台下鸦雀无声。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他继续道,“是不是王大人又要借题发挥?是不是他又想煽动民心?”他忽然从袖中抽出一把剪刀,当众剪下一缕白发,投入火盆,“这是我三十年仕途的最后一点执念。今日我以发祭庙??若新政真为私利,愿我身死名裂,永堕地狱;若此道合于天地正气,请诸位替我守住它,哪怕我不在了!”
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哭喊:“我们守!我们守!!”
就在此刻,一名衣衫褴褛的老妇挤上前,颤巍巍举起一本焦边残卷:“大人!这是我连夜誊抄的《均田议》节录,原本烧了,可我记得!我还记得每一句话!”
紧接着,十几个少年齐声背诵:“赋出于田,权归于民;官非主,法为尊!”
更多人跟着念起来,声音由小到大,最终汇成一片洪流,在寒夜里久久回荡。
王小仙闭目伫立,泪水滑落面颊。
翌日清晨,他召集核心幕僚于静室议事。蔡京呈上一份名单:“经查,纵火者极可能系旧党安插在驿馆的差役,此人已于昨夜失踪,其妻儿亦不知所踪。更可疑的是,火灾发生前两日,延安府突然调拨一批‘修缮银两’给夏州工务局,经手人正是张穆之旧部。”
“又是钱开路,火灭声。”苏轼冷笑道,“他们以为烧一座庙,就能掐断思想?殊不知,越是打压,越有人想看那书中写了什么。”
王小仙缓缓点头:“从今日起,《河朔新政实录》不再仅由官方刊印。我授权所有学堂、商会、村社自行翻刻传播,哪怕一字一句,也要传遍西北每一户人家。告诉他们:这不是我的书,是他们的权利清单。”
他顿了顿,又道:“另外,启动‘火种计划’??挑选一百二十名十五岁以下聪慧少年,分批送往伊克昭草原深处、黄河渡口、西域商道等偏远之地,每人携带一部精简版《实录》,在当地办学授业,三年为期。谁完成任务,谁便是下一任咨议局青年议员。”
众人动容。苏辙低声道:“此举形同另立政教,恐被指‘结党图谋’。”
“那就让他们说去。”王小仙淡然道,“只要孩子能读上书,只要百姓敢质问官,我就算背上‘逆臣’之名,又有何惧?”
腊月初七,大雪封山。王小仙病情急剧恶化,夜间咯血不止,昏迷三次。最后一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被强行抬入内室,李婉儿坐在床边握着他冰冷的手,眼中含泪。
“你怎么来了?”他虚弱地问。
“元朗又来信了。”她轻声说,“陛下亲授他‘经义优等生’称号,并让他在廷试上代读《安边颂》。事后,陛下对群臣说:‘王氏家风,可谓忠孝两全。’还说……若西北再有大功,拟加封你为开府仪同三司。”
王小仙听着,嘴角微扬,却未显喜色。“皇帝终于明白,我不是要他的江山,而是要给百姓一条活路。”他喘息片刻,忽道,“取笔墨来。”
李婉儿犹豫:“你身子……”
“最后一道奏章。”他说,“写完,我或许就能睡个安稳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