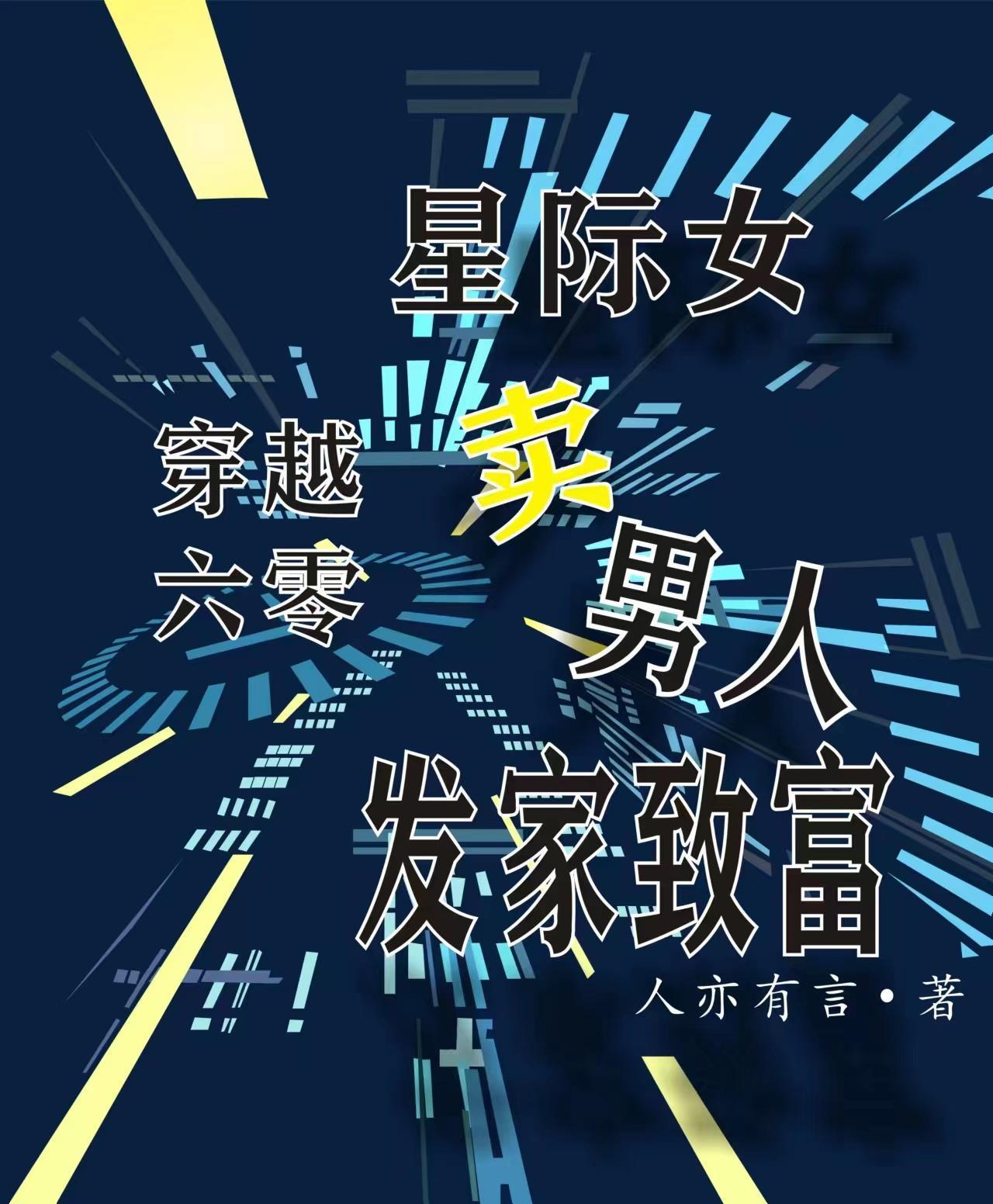02小说网>三嫁太子 > 4050(第46页)
4050(第46页)
比起她的旧伤,这点疼算什么呢?
如果这口子再大些,该有多疼,他又该怎样才能补偿她,怎样才能叫她自逆行的时光中走出?
崔莳也盯着自己苍白的指节,渐渐出神。
直至王絮站在一边,他才若无其事,含笑开口:“我以为,昨日之后,再也无法见到你。”
鲜血逐渐溢出指缝,被溪水冲成浅红的细线。
王絮取来丝巾,要替他包扎。
“不疼。”崔莳也神色一滞,移开了手掌,安静地开口,“你为什么,答应我?”
光斑从叶隙间跌进他眼底,明明灭灭,隐含热忱。王絮垂眸凝视他。
崔莳也有一双不肯后退的眼睛,一道无法回避的目光。这双比溪水更清澈的眸中,带着欣喜、期待、虔诚、小心翼翼……
却没有自私与占有。
没有攀折的蛮力,没有圈养的执念,只是像溪水绕石那样自然地流淌。
欢喜着她的欢喜,疼痛着她的疼痛。
不怪沈令仪说她通诗书而不通气血。
爱的对立面不是恨,而是忘记。有人忘记爱情,有人忘记尊严,而她,早埋葬了自我。
王絮可以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但她依旧与人间情爱,得失离散,与这鲜活的世间有隔阂。
她读得懂情诗里的辗转反侧,却不懂为何有人愿为一茎草木涉险。
她直道草木无情,可此刻眼中倒映着满谷牡丹,丹砂色花团像无数簇跳动的小火苗。
只待某个人的目光将这摧枯拉朽的山火引燃。
“因为,”她说,“冷眼看一切,是很孤独的。”
她正沉吟要回答,人群中爆出一阵尖叫。
沈令仪出事了。
本应和顺的马,忽地奔向山坳。
训马师早去了别处喂马,套马杆尚遗落在一边。
王絮捡起马杆,翻身上了附近的马,冷风灌进领口,却顾不上寒凉。
她记得半里坡有条隐没的羊肠径,可以到山顶去拦截沈令仪。山顶有护栏,底下是深谷。
王絮心中隐约有种不好的预感。
疯马的尾尖已在二十步外。
本该齐整的木栏果真在三步外断成两截。
王絮袖中暗扣几枚银针,数枚银针飞射而出,刺入马腿。
马前蹄在草地上犁出三道深沟,速度只是稍缓。
王絮一扬马鞭,转了个方向。
马奔出二十步时,她终于甩出杆头的绳圈。
绳圈偏了寸许,只套住马的左前蹄。
马匹砸地,狂风呼啸。
沈令仪睁不开眼,五脏六腑都像移了位。
深谷正在眼前。
她撑开一条眼缝,山谷之下,几簇幽蓝的光点突然亮起……是磷火,还是某种蛰伏的野兽眼睛?
至少,再看了一眼牡丹。
沈令仪闭上了眼睛。
马吃痛打了个趔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