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小说网>开国女帝夺权记 现实向 > 和谈下(第2页)
和谈下(第2页)
在观南不在的时候,晏江已经将所有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了。仅仅两日,从衮服到佩剑,从华盖到宫乐,他都找到了对应的匠人。此外,他还理出现有的官员名单,并在空缺的岗位上安排了暂代人员。短短两日之内,他就搭好了整个皇宫系统与文官系统。
观南再见到晏江的时候,他已恢复了最初见面时的从容,但不同的是他多了一层真诚与坦荡。他缓缓稽首,向观南行了个大礼。他说:“臣请陛下暂授臣相印,如今大小官位空缺者共149名,臣需要陛下授权臣去安排人暂代空缺,之后再由陛下选拔正式人员。”
“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职似乎正空缺着,卿可有人举荐。”
“相位至关重要。理应由陛下定夺。臣,不敢置喙。”虽然口上说着不敢置喙,但观南看得出来,他心里的期待。毕竟,这对于所有文人来说,都是无上荣耀。
“爱卿谦虚了,这个位置,非你莫属。中书舍人,拟诏。”
半个时辰后,中书舍人拟完诏书,低头恭敬地放置在观南面前。观南手持着玉玺,盖下了她的第一个皇印。
中书舍人随即持诏念到:
“帝王之临御寰区,必资鼎鼐之臣;朝廷之经纬万机,实赖股肱之佐。矧惟端揆之任,总领百僚;允属具瞻之崇,参决大政。非器识宏远、勋庸昭著者,畴克膺兹异数?
建州知府晏江,秉心贞固,植性端方。学究古今,通六艺之奥旨;才兼文武,负九域之重名。早历清班,屡彰勤恪。外抚方州,则惠流黎庶;内司枢要,则谋协庙谟。顷者总戎边圉,克宣威德,夷狄慑服,疆圉乂安。嘉乃茂绩,简在朕心。
於戏!
舟楫霖雨,朕方寄以济川;盐梅鼎实,尔其调乎鼎味。尚克钦承明命,弼予一人。使风化淳和,彝伦攸叙;兵农协洽,华夏胥宁。尔惟懋哉,无替厥职!
可特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赐金紫光禄大夫,主者施行。”
晏江再次稽首,并说到:“臣定为陛下赴汤蹈火,誓死不负皇恩”。接过了诏书,观南亲手递给他相印,并令中书舍人退下。
“陛下,有见过荀忠吗?”
“见了,他什么都没说。”观南垂下了眼眸。
“如今唐军被定远军牵制住了,无暇南顾。臣以为可借机处理了其军队。”
“如今大吴国力尚虚,不可得罪唐军,我会嘱咐姜明好好监视,待北伐之际,再杀不急。”
"如今唐军被困于西北,不知何时才能脱身。臣不是忧心这一千人的军队,而是担心陛下该如何向天下人说明这政变之事。如果罪臣之首没有得到处置,天下人未必不会怀疑陛下在其中的作用,也会怀疑大吴的法律的权威。"
观南此刻犹如醍醐灌顶,但思忖片刻后,她还是坚持了她先前的想法。
"卿为何如此确定此行不会为我们招来麻烦?"
"臣不能确定,所以臣以为荀忠之部,要么不动,要么赶尽杀绝。而如今,便是斩杀他最好的时机。"
"如今粮食已尽,军队已解散过半。还有许多人的军功没有着落。卿打算那拿什么与唐军作战。说起来,两害相权取其轻,如今,我们只能留着荀忠。"
晏江叹了口气,他又何尝不明白当下的处境。只是世上从来没有两全之法,长期周旋与于各方势力的他隐隐有某种不详的预感。
观南感受到了他的情绪,她纤细的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良久,她有些妥协了。
"如今荀忠所部军纪极其严明,所用之物皆为专供,对于这一千人,卿可有良策?"
"没有。"
"可有中策。"
"没有。可是臣以为还有……"
"好了,现在还不是与他们正面硬刚的时候,这件事还是等秋收之后再说吧。"
"……"
"喏。"晏江退了下去,但不安已在心头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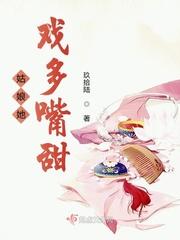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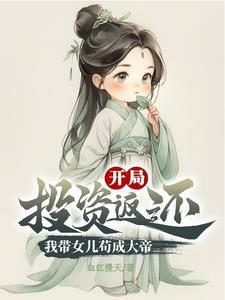
![欢迎光临九州乐园[经营]](/img/6741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