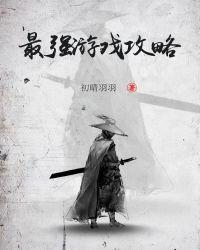02小说网>开国女帝夺权记 现实向 > 叛臣(第2页)
叛臣(第2页)
"先帝,兴许是战事繁忙,但你的政策也应该被广泛实行。"
"那个时候,吴国建立堪堪十年。这十年,先帝南征北战,虽也曾注意到粮食生产,但他更在意的仍然是怎么尽可能减少贪腐,怎么由朝廷搜刮百姓,而不是协助百姓生产。臣滋润也就成了一个无关痛痒的地方官。"
晏江顿了一顿,随后叹息般地说到:"家父就曾违抗先帝在粮食尚未完全成熟时强制百姓交税而被革职,后来,他就因为在瘟疫中赈济灾民,不幸染疾,身故了。"
说到这里,往事再度涌上晏江心头。他也曾是一个爱民如子、克己奉公的良吏,只可惜,在这样的朝代,一个本分的文官没有机会出人头地,而他又是不甘心籍籍无名的,最后,就还是选了一个这样的道路。
"没关系,现在卿的政策可以被广泛推行了。能先和朕说说,卿的务农经验吗?"
"其实很杂,臣一时也记不清了,陛下若是有兴趣,臣回去好好整理一番,明天再交给陛下。现在,还是先说说外面的人该怎么办吧。"
观南见还没有人自行检举,便加晏江去带了一句话:"若是日落时分还没有人检举叛国者,屋外诸臣都要被挖掉一只眼睛。"
晏江走到殿前大道上,对着吓破胆的重臣大声说:"传陛下口谕,若是日落时分还没有人检举叛国者,屋外诸臣都要被挖掉一只眼睛。"
"卑职是不是也可以去检举他人?"
"那是自然。"
"臣滇路转运使,先检举下属于战时,向敌军寄信。"
"什么信?"
"云贵之地的水路布防。"
"你为什么没拦住?"
"臣当时不知道此事。"
"那你现在是怎么知道的。"
"臣后来发现臣的地图被人动过,后来将那叛贼严加审讯,这才发现。但臣不敢上报,怕被牵连。"
"他信里透露了那些内容?"
"水路图,海运路线,和沿岸的军队部署。"
"啊~是这样啊,怎么,你见过那信?这么清楚?"
"啊,不不,臣是审讯中才知道此事的。"
"无妨,既然你是第一个检举之人,朕赏你一腰带。之后会派钦差大臣去调查的,莫耍花招。"
"是是是,臣告退。"
众臣见到这人全胳膊全腿地出来了,全一拥而上,将叛国、渎职、贪污、枉法全说了个便。甚至有人把读书时偷了领家的鸡都说了出来,观南一直忙到了夜里。
"这听了一天,也算是开了眼了,这么小的官职,原来还可以这么贪。啧啧啧,这人,可真是无利不起早。"观南伸了个懒腰,趴在堆满了卷宗与札子的案牍上,揉了揉布满红血丝的眼睛,打了个哈欠。"
晏江听了这话,开始有些害怕。不过这份恐惧随即就消逝了,毕竟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找了一个替罪羊,更何况他如今深得陛下信任。有什么情况,他也可以提前得知。
"我原先还以为,这朝中多少还有几个忠臣,但如今看来,竟只有唐氏父子真心忠于陛下,还真是令人伤感。"
"不要紧,只要卿还是忠于朕的,不就够了吗?"
晏江笑了笑,说到:"这中央几百位臣子,只有臣,能有幸获得陛下的信任吗?"他直勾勾地看着他的陛下,似乎是想弄明白这份信任是否真的出自真心。
观南没有注意到了他复杂的神情,却也只是敷衍地回应:"不只有卿,还有唐氏父子,朕真心感谢愿意在那个时候为朕稳住局面的你们。"
是啊,在那样的情况下稳住局面,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忠臣,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将自己卖个好价钱罢了。所幸,他也只是暗中帮助了一些唐国间谍,并没有将后路走死。只要他不说,她就永远不会知道那些事。
只是,此时此刻,一种异样的情绪在心里悄然升温,她还相信唐氏父子吗?他突然又感到了一阵落寞,这让他吓了一跳,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对陛下有了超出臣子的爱恋,超出对官位的期许,他试图弄清这异样的情愫自何而来,却听见一身闷响和呻吟。
连夜的暗中准备已足够劳累,观南的头也因此越来越低,然后一不小心,就磕到了桌子。晏江笑了,他走上前去,揉了揉她磕着的头,将她抱到了榻上。自己继续处理那堆积如山的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