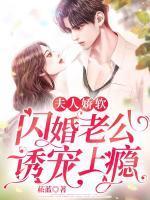02小说网>窝囊废攻重生日常 > 2030(第15页)
2030(第15页)
“王爷,其实我有一事不明。”薛龄君想了想,又说:
“皇长孙被送出京城时,安宁郡主尚且未出生,多年来二人也不曾见过敢问安宁郡主又是如何认出皇长孙殿下的呢?”
“此事说来话长。”襄王说:“当初那孩子被送出京城时,皇嫂曾经将一把寄名锁塞进了他的襁褓里。这寄名锁天下只有一把,极其珍贵,图纸如今尚且还在东宫之中,想必是安宁将那把寄名锁的样式默记在心,见到有人佩戴此物,才认出的。”
薛龄君点了点头:“原来如此。”
“如今,皇兄已经让元双带着那孩子回来了,等那孩子回来,一定要好好补偿他才行。”
襄王伸出手,拍了拍薛龄君的肩膀,和颜悦色道:
“等那孩子回来,我就引荐你见他。他今年约莫也是十七八岁,与你年岁相仿,你在他身边,不仅要是最忠诚的臣子,更要是最贴心的良朋。”
他这番暗示,是要提携薛龄君的意思,薛龄君心领神会,拱手道:
“多谢王爷。”
他没忘记自己今天来找襄王是要做什么,顿了顿,又道:“王爷,其实我今日来,是有一事要报。”
“你说。”襄王今天心情不错,很爽快道:
“有什么要紧事么?”
“王爷前段时间让我去探探那马夫的底细,我已经探知清楚了。”
薛龄君说:“这人原是青州人,其父为一茶商,家中原先富过一阵子。后其父经商失败,家境败落,他便被一家人所收养,改名武思忧。后来青州遭遇百年一遇的水患,家中房屋皆被冲毁,一家人无处可去,便逃亡最近的云城,在路上,父母与弟弟皆感染瘴气而亡,他原本病重,却意外被如今的娘子所救,侥幸活了下来。”
“哦?此人身世竟如此坎坷。”
襄王唏嘘:“那他们在云城呆的好端端的,如何会来京城?”
“说是来寻亲。”
薛龄君说。
“原来如此。”襄王说完这句话才反应过来:
“他有娘子了?他成家了?!”
“对。”薛龄君说:“我观察了他这段时间,他本性不坏,对郡主也并无那样的心思,而且似乎与家中的娘子颇为恩爱,我与他相熟之后,他便放下戒备,与我提起家中事,言语间屡屡提起他家娘子是如何如何贤惠美貌,对自己已经娶妻之事并不遮掩,若是他存心想要攀龙附凤,约莫不会如此大张旗鼓地将自己的娘子展露人前。”
“那琼华此番便是痴心错付了。”襄王踱步坐回圈椅上,掌心摩挲着把手,道:
“那此人功夫如何?你试过了吗?”
“试过了,功夫不错,若参加武举,最差,也应该能得二甲的名次。”薛龄君回忆。
“也是,若是功夫不好,当初就不可能从贼人手里救下琼华。且你瞧人的眼光一向不差,我相信你。”襄王拍了一下把手,似乎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也罢,那我就不去见他了,直接给他写一封举荐书,让他去参加武举罢。”
薛龄君很上道:“王爷慧眼识珠。”
襄王道:
“他愿意豁出命救我儿,说明此人忠心;能从贼人手里救下,说明功夫不错;又没有挟恩图报,意图以此蛊惑琼华,说明此人对他的娘子坚贞。这样的人,想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言罢,襄王就招手让人上前来磨墨,拿起了毛笔,道:
“文宣,辛苦你到时候将这封举荐信交给武科院,顺便传个话,让那个武武什么来着的去参加武举。”
薛龄君道:“愿为王爷分忧。”
一炷香之后,薛龄君拿着那封举荐信走出了书房。
梁琼华已经站在门口等了好久了。
他似乎是提前知道了什么风声,见薛龄君出来,兴冲冲地提起裙摆走过去,道:
“父王是不是答应举荐武思忧去参加武举了?”
“王爷答应了,还托我转交举荐信。”
薛龄君颔首:“我先去给武思忧传个话,等会儿就去武科院。”
“你不用去找他了,我去找他,我,我亲自转告他!”
梁琼华兴奋的脸颊红扑扑的,看起来真的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