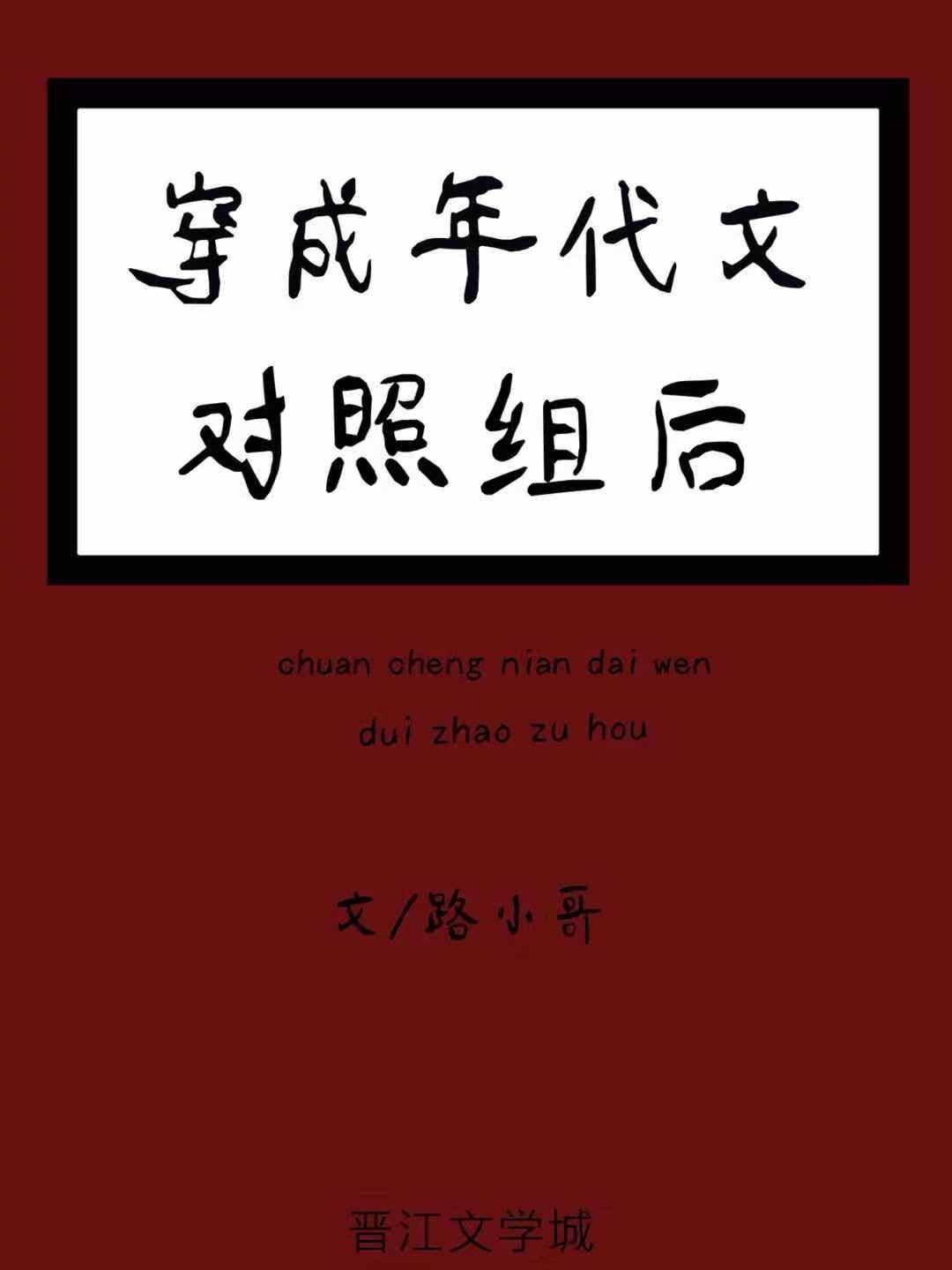02小说网>万人迷在邪神的乙女游戏[人外] > 7080(第7页)
7080(第7页)
倏忽之间。
另一道雪白的人影紧随其后,银灰色的鳞刺和修长的骨尾势如闪电地扫来,趁他捞人时击中了毫无防备的肩背,划出老长一道惨烈的血痕。
“今天,你别想走。”
温润带笑的嗓音显得冷意十足。
“……”
那道清浅的眸光望来,宛如一汪水碧的春水。
“郁姣,留下。”
贺兰铎轻声道。
“想得美。”
松狮冷笑。他一甩黑袍,将郁姣严严实实地裹住,不露一丝缝隙,简直像护食的狗,抑或是害怕心爱之物被抢的小孩。
“……郁姣?”
一声置身事外、后知后觉的低沉嗓音响起,带着无法掩饰的诧异。
聂鸿深那张谋谟帷幄的俊朗面容露出一丝意外。
看着高大的男人以强势的姿态抱着怀中的女人,他脑中电光火石一闪——
皎红月、开场舞、蒙面的男人。
“幻梦中的人是你?”
他沉声问。
虽是疑问句,却带着笃定。
见状,松狮夸张地扬起音调:“原来聂先生也在啊,都没怎么露面啊?也是,阴暗的虫子就该缩在角落。”
一席话说得抑扬顿挫,拉足了仇恨。
聂鸿深面色幽沉。
“……”
他向来成算在心、未曾失手,此时却搞不清楚忠心耿耿的属下为何轻易叛变,不仅胆大包天地闯入神月蛾,还在幻梦中戏弄他。
要是郁姣看到他的神情、知道他的所思所想,必定会嗤笑出声:
面对这种压榨员工的上司,不跑难道嫌命长?
而且拜托,您哪位?压根在幻梦中没注意到您好吗。
但她此刻被松狮裹在黑袍中,什么都不知道,只能听到——
“郁姣,回来吧。”
熟悉的温雅嗓音款款挽留。
不待松狮讥讽,贺兰铎扬声道:“你以为这整日蒙着脸、见得不人的家伙就是什么好东西么?”
“……”
贺兰铎一字一顿:“反抗军里,有那么多人需要[甘霖]、[火种]和[耀金],他开出天价要拿你做交换。”
郁姣心下骤然一沉。
明显感觉到抱着她的男人僵硬一瞬。原本宽厚温暖的怀抱似乎成了一张吞噬她血肉的大口,讥讽着她的天真。
就连那包裹着她的黑袍,都像作茧自缚的报应。
郁姣冷漠望着黑袍透光的缝隙。脑中划过种种被她忽视的迹象,逐渐串联出一个荒谬的真相。
而这人还低声说着:“郁姣,相信我,我回去给你一个解释。”
“……”
“啊,原来如此。”
聂鸿深支着下颚,似笑非笑地看戏,学着松狮方才的语调、回击道:“原来松狮先生也不过是一只卑劣阴暗的虫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