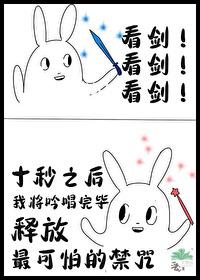02小说网>海棠花未眠 > 第86章 全文完(第2页)
第86章 全文完(第2页)
沈澈贴近她问:“养多久?”
“养一辈子喽。”贺羡棠一脸淡定,“总不能结婚离婚结婚又离婚,唉——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沈澈盯着她看,忽然又把她抱起来,大步走向卧室。
床垫承受两个人的重量,起起伏伏,贺羡棠的手松了又紧,攥着床单被罩以及一切她能抓住的东西,最后被沈澈握住。
灯光晃眼,贺羡棠只好闭上,一切触觉就更敏感了。不知过了多久才结束,她脑海中一片混沌,沉浸在剧烈的快感中缓不过来神,只听见沈澈闷闷地在她耳边笑,讲:“舍不得我呢,bb。”
贺羡棠“嗷呜”一声埋进被子里。
托沈澈的福,到瑞士的第一天,她睡得很香甜,丝毫不受时差影响。
第二天早晨一醒过来,贺羡棠就被人七手八脚地推进衣帽间,她起猛了,头晕,眼前一阵阵地发黑,等缓过来才看见面前一条……缎面白裙子。
像婚纱。
抹胸的款式,腰间捏了褶,蓬起来的裙摆就像一朵花苞,泛着光泽的面料上用珍珠钻石和蕾丝钉着错落的小花朵,很长很长的拖尾。
等人拿出一条轻盈的花朵翩翩的头纱时,贺羡棠终于确定了,这就是件婚纱。
裙子很重,要好几个人帮忙才能穿上。
沈澈等得焦急,点了支烟,克制着推开那扇门的冲动。推开窗,凛冽的带着雪味的空气冲进来,吹散了微弱的烟草味。
一支烟燃尽,门开了。
贺羡棠拎着裙摆走出来。
头纱是整个盖住的,虽然透明,但终究是隔着一层轻纱。沈澈想起在brighten的高定屋里遇见她fitting那次,礼帽也是这样遮住了她的面容,那时沈澈就在幻想这一天了,简直让人无法克制撩开头纱亲她的欲望。
贺羡棠被身边人塞了一束铃兰捧花。
她小声说:“我就知道你在憋着件什么事。”
沈澈回神,没有刻意克制,撩开她的头纱亲上去。贺羡棠尝到他唇齿间薄荷的烟草味。
贺羡棠轻声问:“不是说这次不办婚礼了?”
他们离婚的消息就没对外公开,再次注册结婚也是一切低调从简,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办婚礼。
沈澈摸着她的脸颊:“我还是想补给你,补一场起码是真心在讲誓言的婚礼。”
“婚礼不能这样的。”她说。
沈澈问:“应该怎样?”
贺羡棠回忆上次那一场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的世纪婚礼:“这个时候应该有伴娘堵门。”
沈澈一下也不错眼地看着她:“那我们回香港再办一场。”
贺羡棠说:“还是算了。”
她摸到沈澈手心的潮湿,笑他:“你紧张吗?”
“只是觉得不真实。”沈澈又侧过头吻她。
人在最接近幸福的时候是这样的。总疑心一切是假的,是镜中花,是转瞬即逝的绮丽梦境,是波光一荡就碎掉的月。
他第一次婚礼,不知道珍重是什么滋味,按部就班地走流程,来往宴请。所有亏欠的一切一切,都在今天还回去了,三十多岁的人,还像个得到心爱的玩具就不肯撒手去睡觉的小孩儿一样。
沈澈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走了,去结婚。”
这座小镇只有一间教堂,被沈澈布置成堆满鲜花的样子。十一月实在很难在瑞士见到这么多的鲜花。
现场用了很多兰花和玫瑰装点,蜿蜒成鲜花瀑布,有点像盖茨比迎接黛西时的那个场景。
贺羡棠也不知道他出了多少钱才被允许在教堂里这样布置。
挽着沈澈的手缓缓走进,一路花香。
窗外是皑皑雪山,教堂内鲜花盛放如春。这场婚礼没有宾客,证婚的只有当地的一位牧师。
他一袭黑袍,用德语讲誓词,浑厚庄严的声音伴着钟声飘向穹顶。
“沈先生,贺小姐,你们是否愿意谨遵结婚誓词,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或健康、美貌或失色、顺利或失意,都愿意爱ta、安慰ta、尊敬ta、保护ta,并愿意在你们的一生之中对ta永远忠心不变?”
贺羡棠定定地望着沈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