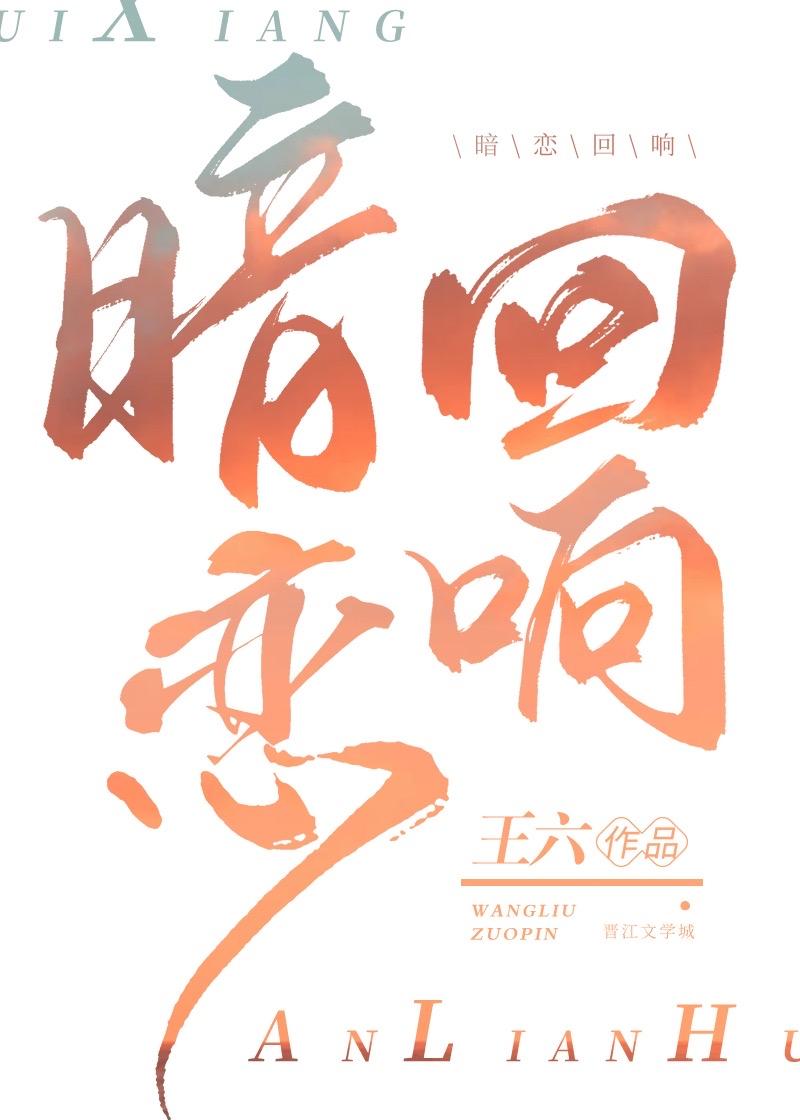02小说网>朕未壮,壮即为变! > 第97章 子为王母为虏(第4页)
第97章 子为王母为虏(第4页)
“虽然最终未能成行,但戚夫人、赵隱王母子,却是真真切切爭取过促成此事的。”
“正所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在高皇帝驾崩、父皇即立后,皇祖母秋后算帐,惩治戚夫人、赵隱王母子,是题中应有之理。”
“一一甚至是非惩处不可,且罚的越重越好。”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警醒后来的后宫姬嬪、庶出皇子:非皇后、嫡皇长子,便不可凯大宝。”
“往远了说,这是皇祖母,在给后世立规矩。”
“往近了说,也是在警告高皇帝诸庶子、关东诸王。”
“从『杀鸡做猴”的层面来说,皇祖母对戚夫人、赵隱王的手段,固然残酷,却算不得不妥。”
刘恭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自是惹得吕太后欣慰的点下头。
便带著自嘲的笑意,一阵摇头晞嘘:“难得刘氏的男人,还有皇帝这么颗独苗,能念著朕的好。”
“只是当年之事,却並非皇帝所想的这么简单。”
“戚夫人,赵隱王,朕固然是要惩处的。”
“但原本,是无需以如此狠辣手段一一甚至是无需伤及其性命的。”
-朕原本的打算,是將戚夫人囚於宫中。”
“也非真的囚禁。”
“就是让戚夫人在永巷,做一些春米、洗衣之类的粗活,搓搓那贱妇的锐气。”
“再以戚夫人为质,迫使赵隱王不敢行悖逆之事,对朕言听计从一一老老实实做先帝的好弟弟、我汉家的好赵王。”
“真正让朕下定决心,不惜以残暴手段,处理戚夫人、赵隱王母子的——”
说到此处,吕太后只微微低下头,抬起左手。
用右手翻起左侧衣袖,露出缝在衣袖內的一张白布,揪著白布边沿猛地一拉。
將白布从衣袖內侧撕下,神情满是阴鬱的递给刘恭。
待刘恭接过白布块,都还没来得及细看其上的猩红血字,便见吕太后再度整过头,望向殿外的夜空。
嘴上,却是无比熟练地,背诵起那张白布上记录的血书。
“子为王~”
“母为虏。”
“终日春薄暮~”
“常与死为伍—”
“相离三千里~~“
当谁,使告汝?”
“这是戚夫人在宫中,自里衣撕下一角,咬破手指以血所著,打算暗中送去邯郸的血书。”
“若非朕派人盯著,將这封血书截获,此书,便会为远在邯郸的赵隱王所得。”
吕太后讥笑摇头间,刘恭却是微微睁大眼睛,满是不敢置信的看著手中,以血写於布上的《春歌》。
愣然许久,才终是瞭然点下头。
“戚夫人,死得不冤。”
“赵隱王,亦如是。”
“太祖高皇帝有制:边墙有变,则赵王自为帅,全掌燕、代、赵三藩兵马一一调动自如,如臂指使;勿需虎符、詔书为凭。”
“若此血书为赵隱王所得,必先以边墙有变为由,尽发戌边三藩之兵!”
“再以『救母』之名引军南下,兵峰直指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