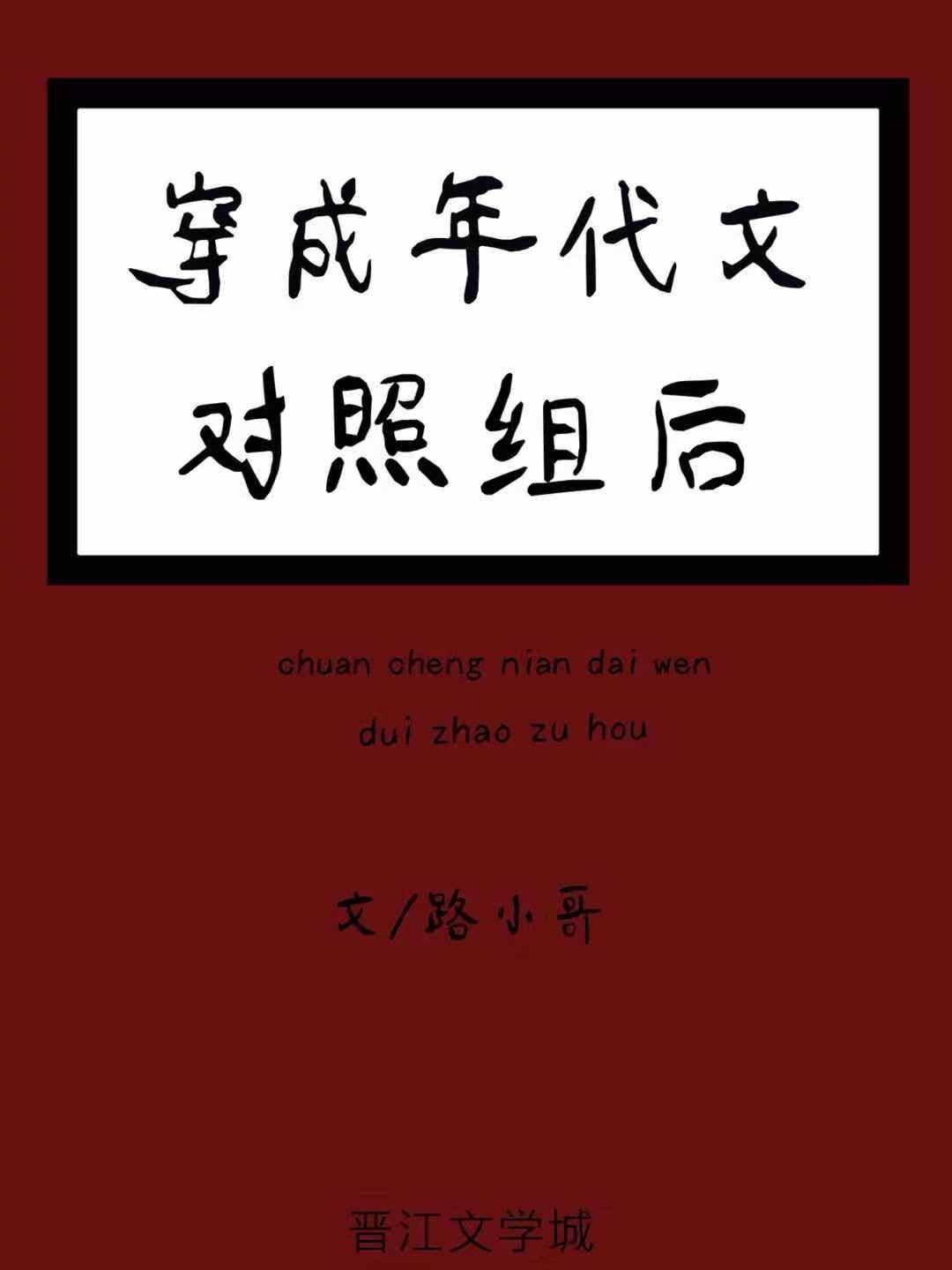02小说网>殿下今夜又失控 > 2830(第2页)
2830(第2页)
里面放着厚厚一摞男子衣物,俨然是几人昨日换下的,罗南说了一大通,但程时玥只明白了一件事。
那便是——他们让她去浣衣。
程时玥双手攥拳,心中对谢煊的恨意更上一层,但她转头,对着谢煊假笑,“郎君,我不是个外室么?为何要去浣衣,若伤了手,可如何是好?”
谢煊的眸子就盯着程时玥看,看清了她掩饰下去的愤恨,却不以为然,他挑眉,不在乎道:“外室又如何?”
他在提醒程时玥,两人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关系,他也不会对她有一点怜惜。
程时玥咬着牙,才能维持住表明的平和,为了不浣衣,她又豁出去,带着点嗔意撒娇道:“郎君~咱们高家又不是没钱?为何要我亲自做?”
“咳咳……”罗南咳了几声,有些心虚,当然是接触的陌生人越多,暴露的风险就越大。
此女日后利用完,杀掉就解决了,多来人还要多费心威胁,他们殿下嫌麻烦。
他当真……从未见过如此不知分寸、厚颜无耻的女子。
子弦和程时玥小声解释,他们郎君行商,继母觊觎家产,妄图害死郎君,所以,要在漕县暂避几月风头。
因着睡前哭过,程时玥眼睛微肿,但醒后已经接受现实,只想着能好好保住性命。
她在心中疯狂盘算,行商就意味着有钱。姜国对商者宽和,后嗣亦可为官,不受歧视,故而,从商者甚多,国富有余。
可她听闻东淮商者为贱,子孙不得入官场,甚至衣着配饰都有所限制。
但此刻,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商者离农本,四处游历,按照子弦所言,他们一行人只会在此呆几个月。
这时外室的好处便显然出来,几月后,她留在此地,岂不是逃走的大好时机。
程时玥又偷偷瞄了一眼静静立于窗边的谢煊,昨晚月色昏暗,看得也模模糊糊,不真切,如今仔细去看,他长得算是可以。
身姿欣长,宽肩窄腰,他面庞线条亦柔和,气质干净,瞧着是个温润好脾气的郎君。
昨日,也是这点给了程时玥错觉,看他好说话才求上他,她以为这样的郎君不会太过为难人。
但今日细细看来,虽然装得温和,但眸中时而翻涌的阴沉是无法骗人的,他定然心机颇深,手段狠辣。
谢煊侧头,黑眸正好与偷摸打量他的程时玥对上,她不自觉打了个寒颤,随后赶紧转头,认真听着子弦的话。
她心中默念,算了,算了,几月而已,忍忍就过去了。万一遇见了来寻她的人,说不定还能早点回去。
落在他手里,起码比在青楼应付那些肥头大耳、亏空身子的油腻男子强。
子弦说,他们最近都要住在民巷中,程时玥想想就觉杂乱,但这郎君是商者,不能明面奢靡也没办法。
程时玥站起身,没人服侍,她只好自己动手理了理外袍。
往日她的贵重蚕服、深衣穿都穿不过来,更别提沾上尘土的男子衣物,但此刻,程时玥直接将昨日的外袍披在身上,完全没有还回去的意时。
罗南无法忍受,只觉程时玥不要脸面,虽然还回来,他们殿下也不会再要,但对方根本没打算还,还理所应当,这就是另外一回事。
他出言,“喂,那边的。”
程时玥闻声四处看了看,这处除了她们四个没有旁人,她这才确定,对面这个浓眉大眼,高大方正看起来傻乎乎的人是在叫她。
外袍逶迤托地,将整个人都罩得严严实实,程时玥也没了昨晚的委屈,境遇一改,没有生死的危机,往日的矜贵又出来了。
有人这样没礼貌地喊她,她已经有些许不悦,但在此处也只能忍下这群粗鲁之人。但她还是下意识微微仰头,“何事?”
问完,她站在门口,转头正对着庙门,远眺着,只余一个侧脸。
罗南突然有种平常殿下问话的错觉,他顺着程时玥的视线往外望,黑黢黢一片,只有几盏破旧的灯笼被风扯着晃,完全没有一点值得看的景色。
程时玥一路的紧赶慢赶,与丁炎几乎是同时到达老医者的家门前。
“叩叩。”
敲门片刻后,老医者便来开了条缝。
“又有何事?那犬不是早便治好了么?”
“老人家,在下方才在路上救下一位流民,因着身份特殊,在下不放心将他放去医馆,便想到了您。”程时玥压低声道,“事关重大,在下想来,殿下是信得过您的。”
老医者一边转身回屋,一边嘀咕道:“上回捡了条狗,这回又捡了个人,你可真是四处捡啊。”
他虽是这么说着,门依旧是敞开着没关。
丁炎倒也机灵,见此情况,立刻将那人从车上拖了下来,扛进了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