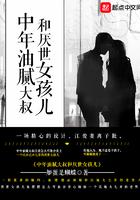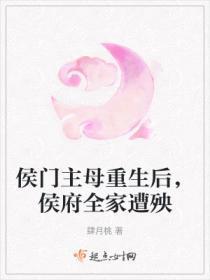02小说网>重燃2001 > 第459章 危棋局前问初心(第4页)
第459章 危棋局前问初心(第4页)
“安安心心坐好,睁大眼睛欣赏本大爷的表演就行!看我如何在王老面前装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逼!”
他咧着嘴,露出洁白的牙齿,笑容张扬得近乎刺眼。
然而,这层被他精心涂抹在脸上的“轻松颜料”,能骗得过一些不相干的人,却绝对骗不过近在咫尺、对他本性了如指掌的刘蒙蒙。
她太了解他了,他那深邃眼底深处一闪而过的沉重,一丝都瞒不过她锐利的目光。
当然,更骗不过他自己。
他那颗高速运转的精密头脑深处,那如覆盖着深厚冰层的贝加尔湖下暗流般的汹涌波澜,从未有片刻的停歇。
此刻,反而因为目标的逼近而愈发湍急。
压力如同千钧重石,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楼上的那间病房里,躺着的那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做王选。
这个名字本身,就沉重得如同山岳。
这个名字,也意味着太多太多。
它是“汉字信息处理与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者,是中国印刷技术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时代的革命性人物,是国家科技创新的丰碑。
他是真正的“当代毕昇”。
那份沉甸甸的第二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荣耀,获取时间仅在开天辟地的袁隆平、吴文俊之后。
这份足以彪炳千秋的成就本身,就足以让任何心怀敬意与野心的年轻人肃然起敬,感受到一种沉重的历史重量。
但更重要的是,“王选”二字后面紧跟着的,是“燕大方振集团实际掌舵人”这个更具现实影响力的身份。
燕大方振集团的前身,是1986年8月燕京大学以微薄的40万元自有资金注册成立的“燕京大学理科新技术公司”。
在那个大学科研经费捉襟见肘、科研成果难觅转化渠道的年代,它应运而生,成为“根正苗红”的产学研探路者。
1992年,它正式更名为“燕大方振集团公司”。
王选那项划时代的激光照排技术,正是方振崛起的基石。
在其后的十五年里,方振依托燕大的科研底蕴和人才储备,如同一艘搭载着先进引擎的巨轮,乘风破浪,版图不断扩张。
从激光照排的核心业务,广泛涉足pc制造、新闻采编系统、远程传版技术乃至各个领域的技术研发和投资,成为了多元化、集团化的科技巨擘,鼎盛时期在全球华文报业市场占据了惊人的80份额,旗下拥有多家上市公司,风头一时无两。
可是,企业的发展有高峰也就有低谷。
随着方振走向资本化和市场化,股东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弊端。
二股东渠万春以“科学家不懂经营”为由,要求王选让位给‘具备国际视野’的海派职业经理人。
国资的力挺保住了王选的位置,却未能保住他的搭档、方振集团董事长张玉峰的职位。
作为妥协的代价,张玉峰黯然卸任,大批“懂资本”“懂市场”的‘具备国际视野’的海派职业经理人入驻方振核心管理层,掌舵方振科技、方振控股、方振数码等核心上市公司。
王选虽未被完全扫地出门,但自此淡出了方振的日常管理,方振集团进入了所谓的“后王选时代”。
资本的游戏开始了。
职业经理人们带来的,是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概念炒作和多元化扩张。
方振的手伸向了证券、钢铁、制药、地产、金融、教育……股价一度从113港元飙升至10港元之上,鲜花着锦,烈火烹油。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
然而,剥开光鲜的外衣,实体的经营却如断崖般坠落。
当炒作的潮水退去,裸泳者显现。
吴楚之对职业经理人的戒心并非空穴来风,方振集团正是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技术巨人辛苦打造的家业,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内被蛀空。
那些所谓的精英们伙同资本,高位套现后潇洒离场,留下的是一个巨大的烂摊子。
一个冰冷到刺眼的数字,无情地宣告了方振的困境:2001年上半年,年营收数百亿的庞然大物,净资产竟为负80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