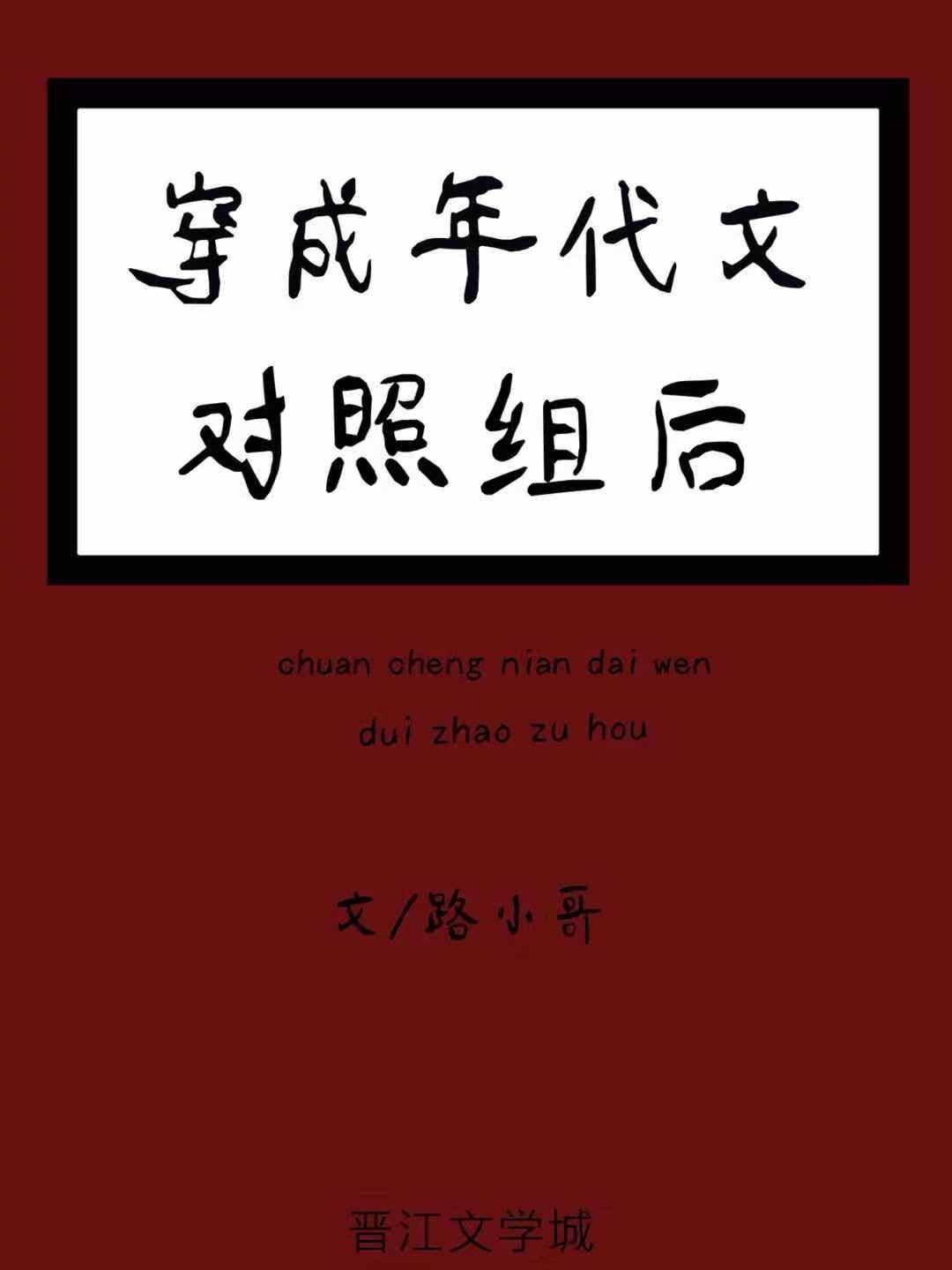02小说网>生涩 > 5060(第2页)
5060(第2页)
“坐。”顾予岑看着楚松砚,却一直没松开抓着他的手。
楚松砚的体温很低,甚至比覆在掌心的雪还要寒冷,像死人的温度。
他觑着顾予岑,慢慢拧动手腕,挣脱顾予岑桎梏的力道。
顾予岑也没强求,干脆松开手。
“你……”
“先坐。”顾予岑打断他。
楚松砚沉默两秒,才坐到长椅的最边缘,身子稍稍前倾着,用胳膊撑着腿,他低垂着脑袋,没再看顾予岑,低声问:“你想要什么。”
顾予岑站在他面前,慢慢蹲下身,仰头看着他。幽暗的环境里,楚松砚的脸被口罩遮得严严实实,漆黑的眼睫还将瞳孔遮盖住,顾予岑根本看不出他的情绪。
但他太懂楚松砚。
很清楚这话代表什么。
交换。
作为他找到那个俄罗斯演员的交换。
“你想给我什么?”顾予岑问。
楚松砚缓缓道:“……我不知道。”
顾予岑倏地伸出手,用手指勾下楚松砚的口罩,然后又用手背轻轻碰了下楚松砚的侧脸。
很凉,很冷。
更像个死人了。
顾予岑张了张嘴,但话到喉咙里,他又硬咽下去,故作不在意地别开脸,话锋一转道:“在《止淋》之前,就听说刘赀廉手里那部《野春恒》准备找你,我看过剧本,挺不错的。”
刘赀廉是近几年的新锐导演,拍摄的风格独特,且更贴近年轻人的心态,惯会用镜头语言来下勾子。
《野春恒》是他得奖后最受瞩目的待定剧本。
“我没准备接。”楚松砚说,“你要是想……”
“嗯,看来是还不够好。”顾予岑说,“那就换一个。”
楚松砚闭上嘴巴,安静地看着他。
过了足足半分钟,顾予岑才再次开口说:“卖身吧,像之前那样。”
之前。
楚松砚的思绪瞬间被拖拽到回忆里。
当初拒绝《难违》后,楚松砚直接接了那部文艺片《沽河》,不是头脑发热后的随意决定,而是它的剧本确实不错。
至少对于当时的楚松砚来说不错。
楚松砚能确认自己的情绪已经无法自主调动。
同楚柏理清关系,间接与曾经的家乡分割连续,身边唯一能说上两句话的,也只剩下个林庚。
但面对林庚,他也是半真半假地应付着彼此,有些话不适合同林庚说,一切影响不好的负面情绪都会影响两人之间的工作关系,楚松砚有自己的顾虑,只能将这些都压在心底。
你真让他不顾一切地吐露,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说什么,又想听到什么。
他只是感觉迷茫。
而这种迷茫恰巧是《沽河》中全程贯穿的。
拍别的如果出了错处,就是自砸饭碗,毁了《皿》造出来的天赋型演员的称号,还不如保险些,挑一个能演绎得差不多的剧本。
不用日夜担忧地死钻进剧本里,还有钱拿,何乐而不为,钱赚够了还不用愁以后买不起冥币,死后总能快活,楚松砚这样自暴自弃地想着。
但在拍摄到一半,就出现了问题。
彻底贯穿的迷茫与压抑,不仅迁就着楚松砚的情绪,也助长他心中的恐惧。
他开始分不清戏里戏外,结束拍摄后窝在酒店里,捧着剧本一坐就是到天明,但眼睛盯着纸张上漆黑的字,脑袋里却是愈发激烈的情绪波动。
频繁失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