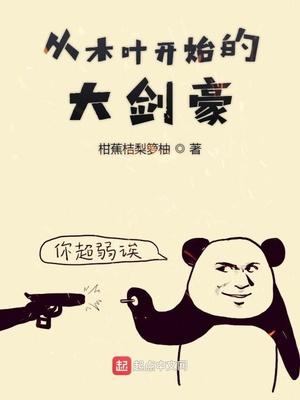02小说网>在柯学世界做钓鱼佬真的很难 > 2第二章(第2页)
2第二章(第2页)
毛利凉介坐在楼下,思绪快乱成了走马灯,看来之前爆炸引起的耳鸣,还有一些后遗症在。
脑子里一会儿浮现出来了有警察牺牲了;一会儿冒出来之前他在楼道里看到的人……
纷乱的思绪如野猫撕扯过的毛线团,在脑海中纠缠不休——牺牲的警察、潜伏的炸弹犯、化为废墟的家、连同那根从未钓上鱼的鱼竿,全混作一团。
毛利凉介坐在临时安置点的长椅上,速写本摊在膝头,铅笔尖在纸面游走,梳理着他接触到的信息:[炸弹]、[人为]、[踩点]、[可疑]……
“小朋友,你住哪一层?”做笔录的警察半蹲着问他,似乎在做什么档案统计。
毛利凉介却正有发现要告诉这个警察,他快速地翻到速写本前一页:
简单的黑白铅笔画里,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缩在楼道阴影中,脚边露出一截黑色工具箱。铅笔在男人衣角打了个箭头,标注「11月5日17:28,自称维修工但没带工牌」。
“他按过七楼电梯按钮,但最后去了隔壁空屋。”毛利凉介指向画中工具箱的锁扣,“这里刻着「tk」缩写,可能是名字?”
警察瞳孔一缩,没想到只是想关心一下落单的小孩,随手一问就是一个重要线索,抓起对讲机匆匆离开去汇报,临走前给了毛利凉介一个联系方式,方便后续联络。
毛利凉介撕下这页速写,妥善保管,希望对警察的破案有帮助。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邻居们陆陆续续在警察的指引下回家收拾东西。
只有毛利凉介一个小孩可怜巴巴的坐在那里,一个警察还给了他一块毛毯和一杯热巧克力。热巧克力的甜香裹着毛毯的暖意渗入四肢,紧绷的神经终于稍稍松弛。然后他这才发现,他下意识里将刚才爆炸现场的那个,好像失去了挚友的警察画了下来。
——卷发的警察倚着警车,攥着手机的手指关节泛白。凌乱的卷发、咬出血痕的下唇、脚边散落的烟蒂,四散的爆炸风尘。
画到一半,一滴水渍晕开墨迹,他才惊觉下雨了。
“呜……”
细弱的呜咽从脚边传来。毛利凉介低头,撞进一双紫罗兰色的眸子。小边牧浑身沾满灰土,后腿不协调地打着颤,却固执地扒住他的裤脚。更诡异的是,它正死死盯着速写本上的警察,喉间溢出悲鸣般的低吼。
“你也觉得难过吗?”毛利凉介用毛毯裹住小狗,带着它去躲雨。然后用指尖擦去它眼角的灰尘。小边牧突然疯狂舔舐他的手背,湿漉漉的鼻尖贴上速写本上的画像,仿佛要透过纸面触碰什么。
毛利凉介下意识的把小狗抱紧了一点。
这时,一边负责做公寓楼住户登记的警察,似乎并没有发现毛利凉介的毯子里多了一只小小狗,忍不住问他:“小朋友,你联系上你父母了吗?”
回过神来的毛利凉介解释说:“我爸出国打比赛了,现在在法国还赶不回来。”
毛利凉介的父亲是职业网球选手,母亲则是运动康复师,这对“空中飞人”夫妇常年辗转全球赛事。
就在负责登记的警察还想说什么的时候,一个熟悉的焦急的声音喊了毛利凉介。
“凉介!”
毛利凉介一看是舅舅柳生比吕士来了,各种委屈后怕的情绪涌了上来,抱着小狗就冲向了舅舅。
“舅舅你终于来了。”
再怎么成熟稳重,到底还是去医院要挂儿科的孩子,毛利凉介特别伤心,不知是雨水还是眼泪糊了一脸,抱起小边牧用小边牧的脸毛擦了擦,酒红色的小卷毛和呆毛软塌塌的盖在额前,看上去可怜兮兮的。
柳生比吕士不语,只是紧紧地抱住自家外甥。
天知道在医院里给病人做手术,一下手术台接到外甥的电话,听到电话里说“舅舅,我家被炸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还好外甥毛利凉介爆炸发生的时候,人是在安全地带的。
毛利凉介低头摩挲小边牧的耳尖,声音闷在绒毛里:“警察叔叔说房子现在像被蛀空的冷杉,一碰就碎成粉末。我的……不知道还在不在。”
“听警察的,过两天再去拿东西。”柳生比吕士抱紧了外甥。
“那我明天上课怎么办……”毛利凉介背着钓鱼装备,抱着小边牧,亦步亦趋小尾巴似的,跟着柳生比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