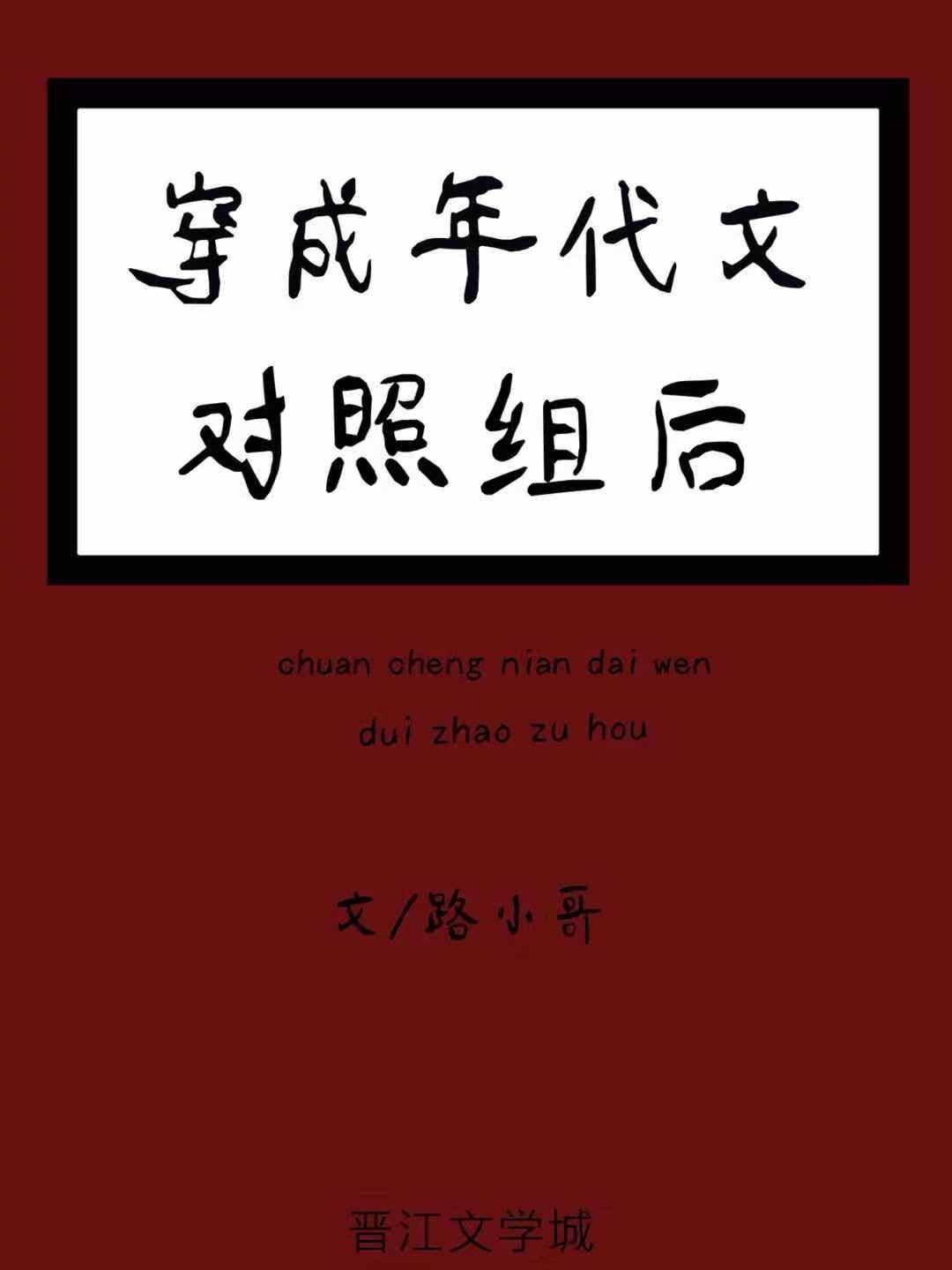02小说网>罚酒饮得 > 10薄命女(第2页)
10薄命女(第2页)
周夫人唤来女使文竹,让她将晏怀微送回晴光斋,一场要打要杀的闹剧至此落下帷幕。
文竹扶着晏怀微回到晴光斋的时候,一进门晏怀微还没如何,倒把应知雪、应知月姊妹俩吓得差点没晕过去。
昨儿夜里明明得了与郡王共枕眠的殊荣,怎得今日却被打成这样送回来了?!
难道是……伺候的不好?
“这是怎么了?恩王打你了吗?他为何要将你打成这样?”姐姐应知雪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查看晏怀微面上的伤,又一连串问道。
文竹低声说:“不是恩王打的,是县主。”
妹妹应知月倒抽一口冷气,小心翼翼道:“你怎么把她惹了?这下可要糟……”
在场诸人谁不知道,乐平县主赵嫣平日里脾气泼辣,是个被宠得没边儿的富贵千金。往日但凡她来府里,雪月二姊妹皆是能躲就躲着。
“我没事,不用担心……”晏怀微说完,先向文竹道了谢,之后便躲回自己那间西厢去了。
西厢不大,陈设也并不华贵,可晏怀微每次关上房门独坐房内,便会产生一种安稳之感。就好像她又回到了在家中做女儿的时候,躲在自己那间宝帘闲挂的闺房内,填词、作画、抚琴、歌吟,无论做什么都是自由的,都是开怀恣肆的。
可惜,那样的日子在她的人生中已经一去不复返——她这辈子再也不可能恣肆自由。
豆蔻少女们总想步出闺房,去看波涛汹涌的人间。可她们不知道,这闺房一旦步出,就再也回不了头。
想着想着,鼻子发酸,眼圈又变得通红。
晏怀微赶忙捏紧拳头将眼泪憋回去,复又起身取了块布巾,对着房中那面铜镜,将面上血痕尘污一点点擦拭干净。
刚擦完,这便听得外面有人叩门。
“梨娘子,你歇下了吗?若是没歇就到竹亭来吧,胡诌给你拿了敷面的药膏。”是姐姐应知雪的声音。
“我这就来。”晏怀微应道。
她换了身干净衣裳,又取出面纱将脸上的新伤旧疤都遮好,这才打开房门向晴光斋外面那间竹亭走去。
亭内坐了三个人,除雪月姊妹外,竟然还有一位陌生的年轻男子。
那男子戴个局脚幞头,内穿白绢中单,外罩一件斜领交襟半袖褙子,看这打扮似乎是刚从马球场下来。
晏怀微面带疑惑地看向应知雪——这人是谁?竟敢在王府四处乱跑?!
未等应知雪开口,那人倒是十分热情地向晏怀微唱了个喏:“想必这位便是才华横溢的梨枝娘子?鄙人胡诌,这厢有礼。”
晏怀微与他见礼,口中喃喃念着:“胡……周……?”
胡诌笑道:“对,就是胡说八道的胡诌。”
应知月“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胡诌听她笑自己,非但不生气,反而乐道:“月妹妹终于肯笑一笑了。笑一笑十年少,人就该多笑一笑。”
应知月倏地把脸扭向旁边——油腔滑调,不想理他。
“晌午我陪殿下去打马球,这会儿他进宫去了,我来向周夫人问安。夫人说你吃了乐平县主的耳光,我说我刚好有一瓶上好的伤药膏,夫人就让我送来给你。乐平县主从小被官家和殿下一起宠着,早宠得没了闺秀模样。下回她若再来寻你麻烦,你就像耗子看见猫,呲溜一下跑没影儿就行。她跑得可慢了,铁定追不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