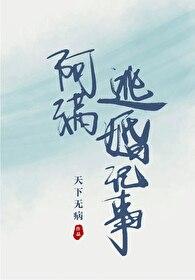02小说网>诱骗宿敌成婚后(双重生) > 第 5 章(第2页)
第 5 章(第2页)
叶拂青的视线从他的手落在他脸上,出声道,“永徽二年,户部尚书李文搜刮民财、贪污国库被查处。大理寺卿审查其案,再揭重罪,三年前李文结党营私,昧了供给粮草,致使定王北疆一战惨烈战败。”
叶拂青提到未曾蒙面的父亲顿了顿,但仍旧神色淡定,继续说,“圣上勃然大怒,数罪并罚,将相关官员悉数惩处,发落数百人,乃称永徵第一大案。而朝议郎谢良平也牵扯其中,举家被贬为庶人,发配北疆以赎其罪。被判当日,谢良平自缢于诏狱,时人俱言‘畏罪自杀’。”
这是京城人尽皆知的案件,也是谢濯重回京城上表的第一份奏章。
尽管最后查明谢良平同李文并无干系,实属无辜牵连,但斯人已逝,哪怕沉冤昭雪也换不回一条人命。为弥补当年错判,以昭天子英明,圣上将原本加官进爵的封赏又抬高,特封他为平远侯。
叶拂青虽不参与朝政,但朝中局势如何变幻却知道得一清二楚。
谢濯许久未开口,叶拂青偏头用眼神示意夕照守在门口,后者依言走到门边。
叶拂青学着他的样子,手指轻敲桌案,等着他的回答。不知他想到了什么,皱着眉头闭了闭眼,再睁开眼时眼睛一片猩红,倘若不是离得近,她半点也察觉不到这人的情绪波动。
“公主再提旧事意欲何为?”谢濯嗓音依旧沉稳冷静。
“‘畏罪自杀’,侯爷可信?”叶拂青收回视线不再看他,淡淡开口,“不过是发落北疆,何至于弃家人于不顾?”
“信与不信不过都是镜花水月,又能改变什么?”谢濯语气平静,刚才的失态仿若是她的幻觉。
叶拂青熟知他一贯品性,在缓缓吐出心中浊气后,沉声道:“他还活着。”
谢濯猛地抬头,用犹如豺豹看见猎物一般的眼神死死盯住她,恶狠狠道,“公主倘若拿此等事唬我,当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自然。”叶拂青一口喝完剩余的茶,说:“我不单知晓他还活着,也知晓他身在何处,以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谢濯瞥了她一眼,也抿了一口茶,冷声问,“公主想要什么?”
“同我成亲。”叶拂青补充道,“不需要你同真夫妻那般待我,只需告诉圣上你愿意同我成亲即可。婚后我们互不干扰,只当这婚约是空壳,我们仍旧井水不犯河水。”
“公主做了如此之多,甚至不惜将秘辛泄露给我,只是为了同我成亲?”谢濯语气幽幽,满是对她的怀疑。
叶拂青管不了他信与不信,冷着脸点点头,端着架子不愿跟他解释太多。她何尝愿意如此大费周折呢,倘若不是这人太难缠,她懒得再将陈年旧事翻出来说。
“我答应你。”谢濯声音无甚起伏,只是一味地盯着她看了又看。
叶拂青紧绷的状态松懈几分,果然对于这种不近人情的人还得使用非常手段才行。
“今日我只能将来龙去脉告知你,至于他的行踪……”叶拂青顿了顿,说,“成亲之后我再告知你。”
谢濯闻言,轻笑一声,语气中暗示意味十足,“倘若成亲后我没能找到活生生的人,公主便休要怪我以下犯上了。”
叶拂青不理会他的威胁,自顾自开口阐明事情的经过,“李文其人心思极深,事情败露前夜曾大宴宾客,于杯中投毒,意欲拉所有人同归于尽。此毒不可解,中毒之人会逐渐失去神智,意识不清,痴傻而终。而你的父亲同他本不亲近,那日却也在受邀之列,如此便也……”
彼时的她方才十一岁,凭着宠爱,在宫中向来是无处不可去,整日贪玩好动,搅得皇宫鸡犬不宁。
那日她翻入早已废弃被禁止入内的荒殿,瞧见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头跪在地上,用手不停地划着木门。
她同他说什么那人都不回答,如此过了半个月,终于有一天对方说话了。
“您是宫中哪位贵人?我想离开这,放我出去吧。您能不能去求求陛下,把我流放到别处去。”
叶拂青也是去求了圣上之后才知晓整件事情的因果。
她将所了解的一切悉数说出,“他不愿以痴傻之状面对你们,又知躲不过受罚,便请求圣上将他囚于废殿之中。但十年过去他未曾同人说过一句话,病情愈发严重,直到我见到他那日,他终于忍受不住,请求我放他出去。”
“整件事情,我所知晓的便是如此。”叶拂青补充道,“从那日算起,他现下应当只余几年可活了。”
话落,她视线扫过谢濯紧紧抓住茶杯的手,手背青筋暴起,似是忍到极致。
“那你为何会知晓他的行踪?”谢濯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