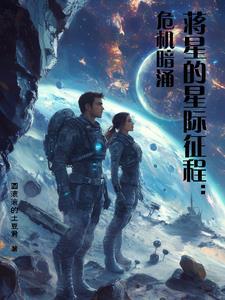02小说网>君欲挽春 > 朝堂纷争(第2页)
朝堂纷争(第2页)
“张尚书所言便是有违其实,下臣自然不敢不满指挥使行为,只是不忍定论匆匆,以为此举有所不妥,若能复得详勘,才可……”
张尚书面对他这滔滔不绝的冠冕堂皇,轻描淡写将其堵了回去,“指挥使奉陛下御旨彻查,当日数仵作下场验明,再有杨仆射仆人亲口所言,当日未有贼人,况杨大人早已盖棺停尸距今数日,若依你言辞,一则颠倒陛下恩德,二为不敬亡者安宁。”
前御史微微眯起狭长的双眼,细褶密纹遍布眼角,“尚书何必如此,本官与中丞,左右不过想替杨大人讨个清白,何必要为我等扣此等高帽?”
“前御史与杨仆射私下交情之深,实乃感天动地,只是而今亡魂未安,再为惊扰,恐怕非鄙人诓言,”张尚书慢悠悠开口。
“你……”前御史却是忽而息了声音,当今圣上最忌官官相护结党营私,张尚书方才这言辞便是暗地里将他往火堆上推。
他心里暗暗冷笑,这张尚书与那指挥使皆是一丘之貉,无所顾忌。
“与其分散人手去想那已尘埃落定之事,不若再谈这江南水灾,恐怕才更有益民生。”
张尚书此言,使得朝堂明里暗里的窸窣声皆是戛然而止,无声的死寂渗透入这朝堂的各个角落。
便是与前陈二人先前早已暗中约定联合发声的官员,皆是不由得停下脚步噤声。
或许怪不得他们畏惧退缩,这江南抗灾一事可不简单,直接便令百官想起先前指挥使将那户部侍郎满门抄斩,一时间众人皆是面露异色,再不敢有所动静。
那等先斩后奏所创之恶行,何等骇人听闻,是以引得先前朝堂掀起轩然大波。
这弹劾斥责指挥使的折子不知凡几,御桌奏疏恐怕早已叠满成山,一人一口唾沫也该足以淹没这朝堂宫殿。
但圣上仁德,不日便以指挥使先前不可磨灭之功绩,堪堪罚去其半年俸禄。
此行一出,百官自然更加群情激愤,对那指挥使更是憎恶,暗恨丛生,却又无人敢直接当堂强硬怒斥指挥使暴戾,罔顾朝纲之举。
只是日后不久,那指挥使便放出那户部侍郎居然利欲熏心贪图赈银,暗地克扣那些用于赈灾的救济灾粮的消息。
江南离上京距离之遥,小吏因承着上头长官的意,加上自己的私心,这层层克扣,放纵贪污,造成救济粮不知多少被中饱私囊。
用于水患维缮堤岸大坝,修建水利,抵御水涝工程几乎难以进行到底,以至于江南生民饱受灾难,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谓苦不堪言。
在此寸步难行境地之下,先前指挥使狠戾手段,以杀震朝堂乱象,此举不知令多少官员暗自惊悚,户部侍郎纵使是主谋,可这朝中之人又有多少暗中苟且。
只怕这头悬刀刃,他们终有朝一日步了这户部侍郎的前程。
是以朝中百官的激烈抗议声才渐渐消退。
“陛下,而今要紧之事,确是这江南一事,虽水涝如今已平息,却不知其中负责要员可否还有隐患,臣还请陛下派出有能之士去往江南,兼查巡抚,革私除尘,杜绝先前营私之举。”
一道声音缓缓从身旁响起,这人令前御史全然不曾意料得到,竟然是刘丞相。
这老狐狸终日和稀泥,今日竟然也会赞成刑部尚书言辞。
刘丞相眼神不偏不倚,直接忽视了身旁前御史的不虞眼神,只是垂首间,眼中闪过一抹复杂情绪。
刘丞相在朝中鲜有立场,但他能当上这百官之首,有他自己的本事。
朝政之事,历来清流中立,中庸平衡之道,被奉为至宝,只是如今,他却是不得不出手。
刘丞相便是刘文琢之父,他向来知晓这好儿子与那白员外交好,交情甚笃。
只是他也是万万不曾想到他这好儿子竟是背着他趟了这浑水。
这江南多水,水患几年一遇,多需未雨绸缭,是以朝堂前些年岁便已外派一位白员外郎南下,亲自处理这江南水患。
白员外白平清在江南便已察觉这赈银出了差错,面对日益严重不可操控的水患,他走投无路之下只好修书一封送到上京刘文琢手中,请他的挚交好友能够出手解困。
刘文琢或许被外人视作纨绔,一事无成,只知交些酒肉朋友,沉溺耽乐,可他堂堂相国之子,上有这在朝为相的父亲,又岂是真正的宵小之辈。
他知晓自己父亲的为人处世,何况这灾情紧急,不容得半点拖延,若是请其他人,恐也会延误。
情急之下,刘文琢便做出一个惊人之举,他决定向指挥使言明这灾情,请他出马。
指挥使的手段有目共睹,但未必是那等残害忠良之人,左右不过是赌上一把。
好在他没有赌错,在此缺人震慑的境地,唯有雷霆方能威慑百官。指挥使出手后,这赈银果然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