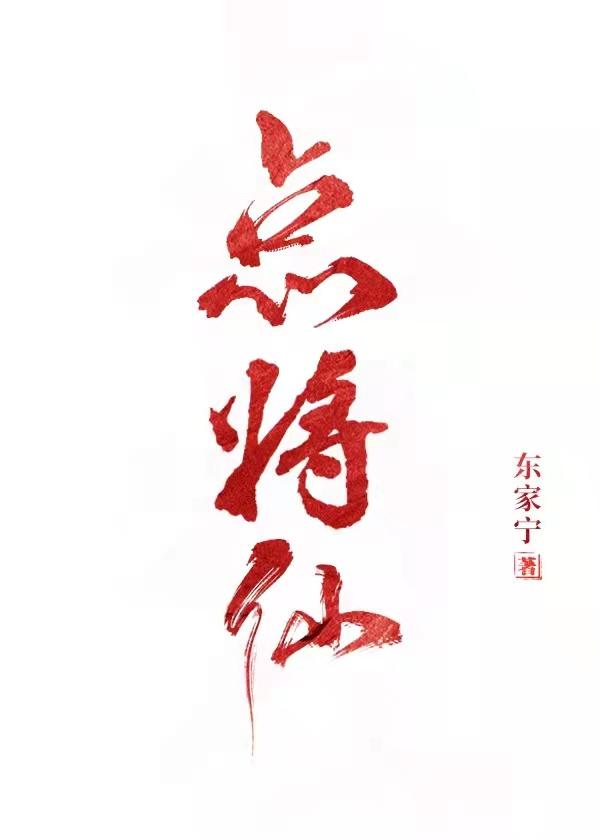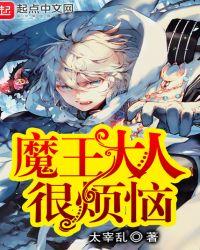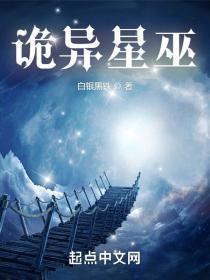02小说网>君欲挽春 > 制灯(第2页)
制灯(第2页)
这般做法的灯笼可不常见,不似上京习以为常的奢艳华丽之风。
“挽春,你这灯笼可不大寻常,”原谙坐在石凳上,忍不住问其缘由。
俞挽春忙活了半天,终于将这竹篾勉强编织成形,她将这笼状竹篾浸没在石槽清水之中,随即取出放置在阳光中静晒。
她缓声开口,“这是我曾经在茳州学来的,时日已久,手法也生疏了些。”
原谙微微怔愣片刻,随即终于想起俞挽春本是来自江南茳州,十岁幼学之际方随俞父俞母回到上京,不久后她们二人才在学堂之中结识。
俞挽春如今应当已在上京久居六年,这六年说长不长,却是实打实离开她诞生之地六年之久。而今匆匆而过,机缘巧合之下,俞挽春到底还是即将回到茳州。
原谙摇了摇头,“莫说是生疏,单凭你方才熟练编织,可比我身旁人都要手巧。”
她不免叹惋,“从前也曾听闻你会制灯笼,只是一直不曾见你做过,而今见到,却是你将行之际。”
这本是无心之言,可俞挽春手中动作却是微微一顿。
六年,她已经离开茳州六年,若说她从茳州带走了什么,这制灯笼是其一,其他也终究隐没。
俞挽春恍惚片刻,却是也忘了她分明知晓这手艺,何以这些年不曾亲自动过手。
只是见到阿酉不久后,她便不由得想起这灯笼,从脑海深处尘封日久的记忆之中淘出当初一丝残存的魂魄,忆起当年岁月。
俞挽春突感脑仁一疼,她忍不住抬手揉了揉太阳穴,将灯笼轻放在桌上,停下来手上的活计。
原谙见状,上前轻轻扶住她,忧心道:“你这是怎的了?”
这股子刺痛来得突如起来,如同万千细针直直扎进太阳穴一般,脑袋仿佛即将从中炸裂开来,疼得剧烈,俞挽春顾不上回应,咬住下唇,脸色苍白。
好在这阵疼痛仅仅停留暂时,这来势汹汹的浪潮潮涨潮汐一般,又收敛起气势,虽说仍旧隐隐作痛,但比起方才,已好转许多。
俞挽春轻轻摇了摇头,“无事。”
“你方才看着可是疼极了,”原谙紧蹙细眉,“莫非是亭中凉风吹得太过,惹得头痛?”
俞挽春轻按额头,“或许罢……”她其实也不知晓缘由,这疼痛来得突然,连半分准备都不曾有。
如同揭开了未愈的伤疤,惹了不可言说的罪孽,使得疼痛缠上身,不得脱逃。
百思不得其解,她只好暂且将之搁置不予理会。
她与原谙闲谈一番,扯了些家长里短,上京糗事,以及一些坊间传闻,不知不觉间心神安定下来,疼痛彻底消失。
今日光线足,这竹篾在日头底下,不到半个时辰便已干透,俞挽春便将其取回来继续手上的活计。
她往竹编的灯身上小心涂上一层细密的桃油,鼻翼微动,混着竹子的清爽,木头的沉香,以及这桃油的柔和气息,杂糅交织,倒是别有一番清新脱俗滋味。
“挽春,看你这般细致……”原谙不由得莞尔,“可是要送给那捕快?”
这些时日的书信之中,俞挽春不曾有意透露,只是偶尔会不自觉地落下几笔那小捕快的痕迹。
毕竟俞挽春少有对男子刮目相看,更是懒得搭理这些人,是以原谙愈发好奇,眼下更是禁不住调侃一声。
俞挽春闻言面不改色,十分坦荡地点头承认。
不消再多说,原谙便多少猜到了几分,只是想到俞挽春即将离开上京,便不禁替二人感到可惜。
俞挽春小心翼翼将皮纸覆上竹篾,一点点细致地将其熨帖在表面,她轻手按压在灯身上,缓缓挤压使之越发贴服。
“对了,挽春,你可知晓上京的白员外不久也要离京了?”待俞挽春将皮纸彻底贴上去,原谙忽而开口。
俞挽春微微抬眸,对白员外这人隐隐有些印象,但一时半会儿却又想不起来。
“先前那画舫的所迎之人,便是他,白员外白平清,”原谙见她这样子便知晓她定是没有想起来,便默默提醒道。
原谙这一提醒,俞挽春倒是想起来了,不过她与那白员外恐怕都未曾有过真正的一面之交。
“他怎的了?”
“他与指挥使似乎要南下往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