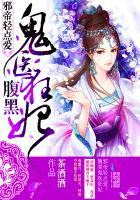02小说网>[民国]那年我妈离婚未遂后 > 仙客来捧花(第1页)
仙客来捧花(第1页)
谢惜予出生没两年,就逢上改天换地的大年景。
大清国倒台,共和已是大势所趋,有志青年无不落辫明志,挺胸昂首加入轰轰烈烈的革命阵营中去。
曾是前朝举子的谢老爷受了打击,上海又是新潮流顶激烈的地方,心灰意冷之下,带着妻女回了杭州,躲入清波门东四条巷避世。
这一年(1912)末,惜予的小弟慎予出生在老宅里,两个孩子无形中为这个死气沉沉的家添缀不少欢声笑语。
又过不到两年,谢老爷的同年王先生亦举家迁回杭州。
闻故人返乡,谢老爷兴高采烈地出了他的蜗牛壳去拜访。
没想到的是,原来王先生跟他不一样,来此不为避世,甚至根本不怀念“老东家”。
王先生人比较开豁,支持共和不必说,早已投笔从商,将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这次回杭州要开设分厂。按他的话叫实业救国。
这下子可把谢老爷惹恼。
当年进京赶考,甲午惨败的阴霾尚且盘桓于国都上空,又遇着倭人逼签条约,他二人同乡,为浙江众举子表率,一齐松筠庵里署名,向光绪帝上书反对丧权辱国之条约。那可是过命之交啊!如今却已只字不提,老友实在没有良心。
相比两家主人中年“反目”,女主人却称姐道妹起来,你来我往,亲热得很。
王家有位公子,年长惜予两岁。谢太太经常带着惜予到王家窜门,一来二去,两个女主人肚里打起了算盘。
就在惜予四岁那年,她同王遗时的婚约由双方父母一锤子敲定。
定娃娃亲后,保守的谢老爷要谢太太尽量不要再带惜予出门,即便是王家,也最好不要。女孩子还没过门就频繁往男方走动,作风未免不庄重,传出去于名声不好。
好在此时小弟慎予已经能走会跑,天天绊着阿姐脚跟头,缠人得紧。谢太太知道丈夫固执,只好点头答应。
于是,自那天起一直到成亲之前,谢惜予再也没有见过王遗时,只偶尔从父母口中听说一些他的消息。
未婚夫妻多年未见还有个原因,王家公子在杭州居住不过三、四年,又被王先生送回上海新式学校念书。
谢家小弟慎予五岁那年,也在谢太太坚持下进了杭州的小学就读。要说谢家就这点最好,女人是能拿得起主意的。
可惜到惜予这边,她福气没这般好,谢太太说话也不管用了,哪怕是王家公婆一起登门来劝,希望有个受新教育的儿媳,谢老爷怎么都不肯松口。抛头露面,成何体统。莫说男女混校,连女校都没得商量。
要念书识字不是不可以,请先生上门授课。
先生由谢老爷亲自挑选,自然同他思想一致,觉着姑娘家家的,字差不多识得,再教几篇《列女传》《女则》《论语》足矣。女子学识渊博,脑袋里想法难免太多,学成秋瑾,于相夫教子无益,更不能考状元,况如今连状元都没得了。
有一天,慎予放学归来,给惜予背了一首新学的英文儿歌,彻底激发她长久以来对父亲的不满。她把想上学接受新式教育的念头再次向父母说了,结果差点讨来谢老爷一顿竹笋炒肉。
直说不成,惜予便用绝食来威胁谢老爷,一向唯姐姐之命是从的慎予跟着一起不吃不喝。
谢太太搓好麻将归家,见一双儿女失魂落魄,小脸比苦瓜还苦,顿时起了护犊心切,同谢老爷撕破脸。谢太太可不同你讲什么道理,丈夫这种爱惜名声的保守派,一哭二闹三上吊才最管用。
最后闹了好几天,逼到谢老爷想离家出走,奈何他舍不得脱离这层蜗牛壳,只好答应让惜予也入学念书。
但有两个要求,做不到免谈。母子三人哪管这个,先答应了。
第一个要求,消息不能外传。
谢老爷甚至给惜予改了姓名,暂随妻子姓顾,户籍寄在她宁波娘家那边,不承认有这个女儿一般。等入了学,上学放课都单独走。由于她念书晚,即便在家识了不少字,其他方面照样落后太多,于是跟着慎予读同一年级。为了不引人注目,姐弟不在一个班级。
谢老爷也没料到惜予的聪明劲会让她一个学期后追上进度连跳两级换班,大叹谁说女子不如男。
可惜,谢惜予在读书上再有天份,中学毕业,考进杭州女子师范不到半年,就被迫休学回家。
这便是谢老爷当年的要求之二,等到嫁人就不能继续念书,于是她不得不变回了谢家的惜予,一个目不识丁的深闺小姐。
目今这样不甚太平的年景,女学生中道休学出嫁的确不在少数。毕竟出于传统的考量,书念得再多也保不了平安,嫁了人好歹有个肩膀可依靠,有个屋檐可遮风挡雨。
一诺千金的谢惜予休学待嫁之际(1927),大学在读的王遗时却是被父亲王先生派人生生从上海绑回杭州。
王遗时无法理解一向开明的父亲怎么就铁了心强迫自己接受一桩封建婚姻。听母亲说,那姑娘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大字都不识几个。连母亲在此事上也是为自己不平的,偏偏开明惯了的父亲为着“君子之诺”要牺牲儿子的婚姻。
想起家族里往上几辈那些个脸孔煞白、嘴唇血红,小脚裹成粽子样,连路都走不利索的太太们,王遗时发自内心地作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