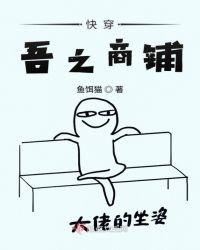02小说网>金枝 > 4050(第7页)
4050(第7页)
祁无忧站着,默默地深吸一口气,绫罗烧焦的气味极为刺鼻。
许惠妃受了惊却很清醒。她不是不怀疑她,只是没有真凭实据。但是现在当着皇帝的面,她非得解释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恰好赶到蓬莱阁不可。
“惠娘娘没事就是不幸中的万幸。”祁无忧道,“只可惜……崇华宫的宫人们大多伤的伤,不能近前伺候。不过您身边的宫女已经被一并救出来了,想必也是些许慰藉。您安心休养便是。”
许惠妃定住。触及祁无忧明澈的眼睛,纵使心中还有疑虑,但得知贴身的宫女也安然无恙,也不好继续死咬不放了。
即使她有心栽赃、指认贵妃和祁无忧加害于她,但母子平安,现有证据不足以一次扳倒她们母女。万一最后她生了个女儿,将来也得仰仗祁无忧,这时还不能得罪。
许惠妃与祁无忧相顾片刻,一切不必言明。她似大松了口气,将噙着的眼*泪咽了回去,“放下心”安歇了。
张贵妃亲自为她掩好床帏,等皇帝最后一步三回头地看了几眼,才冷声吩咐宫人仔细照料。
祁无忧始终乖巧懂事,被烈火和灰烬舔过的双手一直放在身前。皇帝见了,难免不忍。
一家三口放下许惠妃,先后绕过屏风,来到外间。皇帝心疼地执起祁无忧烧红的双手,又发现十指间藏着许多烟灰,万分汗颜:“你也受难了。赶紧让太医来看看。”
祁无忧应下:“儿臣这点伤没什么,惠娘娘无碍就是菩萨保佑。不然,儿臣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高低背个残害手足的罪名。”
皇帝语塞,一时竟难以直面妻女。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他老着脸皮说:“不早了,让驸马送你回去吧。”
说完,又忙着招来左右,要给祁无忧许多赏赐。
祁无忧却立马跪下,总算有了委屈的声调:“父皇给儿臣那么多赏赐,不如收留儿臣,让人家留在宫里住上几天。”
话里话外都是要“回娘家”。
“这是怎么了?”
“父皇不知,那夏鹤婚前就对丹华眉来眼去,也不知夏家是不是一早就想跟王叔勾勾搭搭。”祁无忧说得煞有其事:“刚才在宴上,他又被儿臣抓到现行。儿臣气不过,这才跑下船去。”
她又道:“事到如今,他还想狡辩!儿臣不想见他!求父皇准许,让儿臣留在宫中吧。”
驸马追着公主,跟了一路跟到蓬莱阁,像极了小夫妻吵架闹别扭。
皇帝一听却松了口气,耐心劝道:“不是早跟你说了,你跟丹华置什么气呢?她哪里比得上你。依朕看,驸马那最多就是看了丹华几眼。他到底是个男人不是?这再正常不过啦。”
“刚成婚就闹着回宫里,传出去外面又要说你刁蛮任性。”张贵妃明白过来她的打算,自然装模作样,帮着说和了几句:“到时候,你的名声就更不如丹华了。”
如此劝解了半天,祁无忧才不情不愿地回到花厅里,一见到夏鹤便冷起了脸。
夏鹤一看,竟毫不犹豫地朝皇帝跪下,认错:“都是臣今天惹了殿下不快。否则,她也不会跑下画舫,置身险境。请陛下责罚。”
祁无忧暗暗吃惊。
虽是她刚才灵光一闪,现编出的理由,但也想不到夏鹤仅凭她一个眼神,就能配合到如此地步。堪称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要知道,她这番说辞不仅为解今日困局,也为日后休夫铺垫。
夏鹤与她配合得这样默契,不愧是打了同样的算盘,才能心有灵犀。
外面都不知道画舫里的情形,只知道公主亲身涉险,从火海中救出庶母和龙嗣,得了皇帝泼天的赏赐。就连公主府上下都喜气洋洋,以为祁无忧铤而走险,赚取了仁爱果敢的美名,更获得了帝王的爱重。
晏青早在风中等了半宿。还没上岸,他就听说祁无忧陷于火海,驸马也跟着进去了。他赶到时,正目睹夏鹤扛着一个女子从大火中一跃而出。
他以为那是祁无忧,瞬时丢了三魂七魄,钉在原地一动不能动。直到夏鹤将那女子交给照水,他才惊觉他抱着的只是一名宫女,心里顿时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庆幸。
一种自然是庆幸祁无忧平安;另一种就只有他自己能体会,且难以启齿。
夏鹤以帝婿之身登上了画舫。晏青是外臣,不能参与帝王家事,只得在岸上徘徊。
苦等一夜,听见殿前赏赐了公主,终于松了口气。又等了片刻,总算等到祁无忧和夏鹤一前一后下了画舫。他欲上前,却见夏鹤比他快了几步。
年轻的帝婿一身褴褛,却不显一丝困顿,依旧贵不可言。
不知当年他还是贱民一个的时候,是否就已经具备了这与生俱来的气质。
夏鹤立在如墨的夜色中,亲手为祁无忧披上了斗篷。她也放缓了脚步,甘心让驸马拥着她坐上御赐的步辇。
一双少年伉俪并肩离去,晏青迈出去的腿就这样收了回来。
……
“你可真行。说的比唱的好听,演的比真的还能骗人。”祁无忧走时并不分给夏鹤一个眼神,两夫妻桥归桥路归路。她目不斜视,用他们夫妻两个才能听见的声音讥嘲个不停:“该不会让我说准了,你又想法子勾引丹华。难怪刚才你们两个还一起过来。”
这就有些蛮不讲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