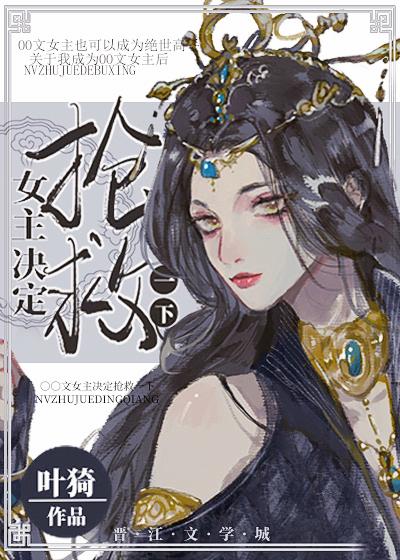02小说网>皇太女 > 110120(第11页)
110120(第11页)
打开城门的动静太大,而这恰恰与皇帝和太女轻车简从的目的相反。
“我刚回到父皇身边的那两年,有时候父皇会带着我到南陵拜祭母亲。”景昭笑了笑,有些怀念的模样,“南陵修的比较省钱,因为它本来是外祖父为自己选定的风水宝地。”
裴令之一怔。
伪朝南下,肆虐北方十二州。饶是南方九州隔水相望,暂时保有平静,不受荆狄侵略,也不可能对荆狄有什么好印象。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荆狄做事实在太不讲究了。
礼制中有一条叫做‘二王三恪’,即新生的王朝要对旧朝皇室保持基本尊敬,封赠旧朝皇室王侯名号,祭祀旧朝宗庙。
这条礼制从上古时期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就连舜帝这样的圣人都在践行,偏偏伪朝慕容氏,将它掀到地上然后又踩了一脚。
慕容诩诛杀贞帝贞后,屠灭桓齐皇室,甚至不曾以像样的礼仪安葬他们,伪朝皇帝行事尚且如此,就更不要指望那些普通的荆狄能干出一点不那么天怒人怨的事了。
桓齐皇室宗庙被毁,皇陵受到波及。不过好歹慕容诩还没有不讲究到那步田地,终究没有真的挖掘陵墓,践踏已经安葬的历代先王。当时贞帝的皇陵依山而建,刚刚修建了三分之一,无论是挖掘还是摧毁,都没有任何价值,所以就弃置荒废了。
大楚立国后,朝廷召集工匠,就在贞帝皇陵的基础上加以改建修筑,是为南陵。
“后来父皇就不带我去了。”景昭说,“因为那时候太后身体还健康,总担心她生出些事来,不便离开京城。”
其实不止如此。
建元二年皇帝带景昭来南陵祭拜时,年幼的皇太女回去就大病了一场。太医说是情志失调、风邪入体所致,僧道方士则说是因为太女年幼,不宜前往陵墓一类的地方,后来还被太后拿来作筏子,扯出了文宣皇后旧事。
皇帝雷霆震怒,发落了太后身边的一批旧人,又再度肃清了伪朝时留下的旧宫人,才算将此事了了。
但不管什么原因,皇帝都不能拿年幼的女儿冒险,更担忧太后暗中做出举动,索性便将此事按下,再不轻车简从离宫。
从此之后,许多年,除去每年祭祀、行猎,皇帝再也没有离开过皇宫。
“这么多年,我们只有每年忌日祭拜母亲的时候会来这里,不过……”
不过,那样盛大的祭祀仪式,一半是为了死人,一半却是为了活人。
皇帝不信鬼神,他年年执意风光祭祀文宣皇后,一大半的原因是为了让活人看。
他越是重视文宣皇后,便越能证明本朝承继桓齐正统,而齐朝与本朝结合的、最为纯正的血统,便是东宫太女。
至于另一半原因,纯粹是景昭私心揣度,并不能作为实证。
她也不信鬼神,但有时遇见上香祈福、叩拜神佛,顺手也就拜了。
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可能,试试也好,万一是真的呢?
倘若真的有那么一线希望,哪怕只是薄薄一线,为此付出再大的代价又何妨呢?
见景昭神情忽而变得有些缥缈,话音顿住,裴令之便作不解状,轻声道:“三日后便是祭祀大典,怎么今夜先过来呢?”
景昭回过神来。
她语调平静,看不出方才在想什么:“不是说了吗,那是皇帝与储君,率领臣僚祭祀先皇后的仪式。现在过来,只是为了自己的心意而已。”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与被皇帝经营多年,如铁桶一般无懈可击的皇宫不同,宫外始终存在着太多不确定的风险。随着景昭长大而储位落定,皇帝和太女绝不能同时离宫。
今夜皇帝回来了,所以景昭带着裴令之离开了。
她挑开车帘,望着山野间起伏蜿蜒如同龙脊般的曲线,淡淡道:“今年意义不同,祭典的抛费远胜往年,想来往后数年间,也很难有这么意义非凡的时刻了,偏你还未正式入宫。”
未来太女妃与太女妃的区别就在这里。
多了‘未来’两个字,景昭依然可以让裴令之堂而皇之地留宿东宫,也可以让穆嫔带着裴令之提前以半幅仪仗往来交际,没有人会纠缠皇太女的这点私事。
但祭祀又不同。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祭典上的每一个位置、每一句言辞、每一场礼乐、每一件器具都需要精心排布,竭力设计,半分不容差错。
裴令之不曾正式嫁入东宫,那么典礼上就不会有他的位置,如果景昭硬要将位次如此靠前的一个人塞进去,很多人的位置都要跟着改动。
景昭不愿意用母亲的祭典来为裴令之抬身价,自然不会硬把裴令之塞进去。
“提前来跟我见见她吧。”景昭轻声道,“母亲她是天下最好的人,没有人会不倾慕她。可惜你缘分稍浅,不能得见她生前风华。”
第116章第一百一十六章玄宫今一闭,终古柏苍……
南陵依山而建,占地广阔,地上绵延着无垠城阙,地下深藏着九重玄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