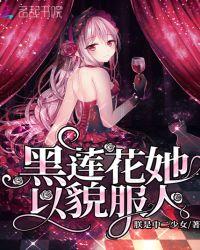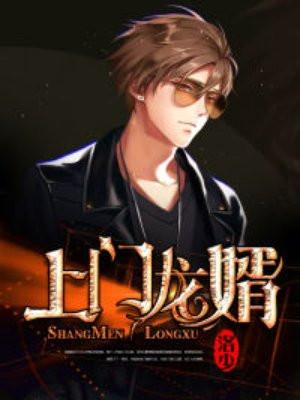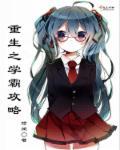02小说网>奔跑着 > 废墟(第1页)
废墟(第1页)
台上的灯光正正打在主持人身上,演讲桌上的娇嫩花束新鲜欲滴,她扶着话筒正在开场,马上就轮到了杨桉。
会议室外的无人墙角处,深黑的正装西裤,内衬简单的白色衬衫,头发扎低,杨桉半蹲着低头看文本,嘴里振振有词地小声念叨,最后过一遍演讲要点。
陈放站在窗边看景色,给她打气:“别紧张,别紧张!”
杨桉尴尬一笑,站直了,嘴瘪着抱怨:“不行,我还是紧张,生怕忘词。”
平常换成他人,她也是这样一本正经的鼓励,现在轮到自己了,手抖脚抖恨不得大吼。
今天的一仗,事关着铁轨更新的大方向,也是她向很多口舌佐证的最好时机,很难打。
“还烧吗?感觉舒服一点没?”陈放伸出手掌等她。
杨桉取下后颈上的退烧贴,放到他手上,不在意地摆手,“能撑,没事。”
她深深地呼吸完,拿上深蓝色话筒走上舞台。
中间宽大的显示屏弯扩覆盖整个舞台的长度,两边的竖向屏幕是杨桉走向舞台正中的画面,不似明星发布会那样粉丝的谜群尖叫,和眼花缭乱的灯牌。偶尔能听见下面的人轻声交谈,调试仪器设备的滴滴声,或者是翻页声,不静穆但是庄重。
主持人言笑晏晏地朝着杨桉点头,示意接场,“有请!”
舞台铺地幕布是暗色绸缎,白光直束下泛冷泛墨蓝,杨桉平静地走到光下,走到中心站定。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讲人兼此项目的负责人,杨桉。”
台下开始鼓掌。
下面坐着的两三百号人都是商界政要,她也从未登上这么大讲台,眼神从后面闪动的十几家媒体往前走,最后几排是设计方,她看到了静薇不顾场合地伸手,毫不在意地用唇语告诉她加油,眉目表情里都是欣赏和赞扬。
看到了陈寒林,内心复杂难明,她真的很感谢陈寒林,能走到这里,这个无私的师傅功不可没,旁边是陈放微笑着朝她握拳的动作。
轻飘飘地看向第一排最边上,观众席的顶灯是淡黄色暖光,与舞台边沿间断隔开,像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谢树半昏半明地坐在那里。
旁边坐着一个从未见过的女人,像无比招人的花骨朵或深色玫瑰,纯黑的礼服不张扬但大气,杨桉的注意力都要多投一点在她身上,以及他正后排一个很年轻的女生,她进来的时候看见人一直跟着他……糟心玩意。
杨桉捏紧手中的话筒,身后全息投影大屏打出会议的主题,她摁下激光笔,同时也摁停自己的瞎想。
“我的演讲将会持续一个小时,前面25分钟是全程论述,可能会有些单调和乏味,大家多担待,中间的空余15分钟间歇休息,大家也可以整理存疑,后面20分钟会由我和我的团队给大家答疑。”
背后大屏变成了报告主题——【尊重废墟,历史与当代共存的媒介:铁轨】
然后是第一张照片,事件切入点,她和陈放一致同意的写实照片。
杨桉笑着走动两步,手掌不由自主地摆动,开始讲述,“调研的时候,我和同伴一路看尽铁轨沿线的商铺、学校、寺庙、菜市场,路过草地、桥梁、公路,有时候浓烈的生活气息和破败的老旧设施交杂,休戚相关但也界限分明。”
“铁轨更像是南城的一条血脉,她链接着沿途的居民,观照着他们的生活,也来者不拒的接收着污秽,随着时代递进以至于日渐没落,血脉干涸生命枯竭,被人遗忘,被历史遗忘,被南城遗忘。”
“而到现在,它变成了很多人厌弃的对象,破旧、贫瘠、根深蒂固、沉疴旧疾……更多地用来形容它,它也只是不声不吭。”
“我们创造了它,同时也毁灭了它。”
进到这里,她看见有人点头,也有人好像准备鼓掌,看到旁边的人都毫无动静,又沉默地放下。
或许不为杨桉的演讲所感动,而是故事里的铁轨似乎是一个温情,而又始终沉默寡言的你我他。
杨桉回头望着屏幕,灯辉映照着她的淡妆,十分相宜,嘴角上扬后又绷平,给大家介绍:“这是沿途的一张广角,当日暮渐沉,一天中的最后一点光亮同时照在铁轨、大厦、小孩、青年、老人身上,他们好像在同我们讲述——生命的不同留存形式。”
“几十年前的铁轨风风光光地开进城市,那时候的人们肯定没有想过这些大家伙有一天是会被人遗忘,惨遭门庭冷落;而现在刺破苍穹直窜云霄的大厦某一天也会油灯枯竭,钢筋混凝土终会坍塌断裂损毁。”
她停顿了一下,引入人进行类比:“就像我们的生命周期一样,小孩、青年、老人,总有新生、过程、逝去,没有什么是永存的,死亡这个话题离我们很远,又很近。当人终变成骨灰时,我们把它洒向山脉、大海、雪原、花海,或者胜葬之后的每年祭奠,我们是这样铭记我们的同类,可是对于我们创造的物质,我们该怎么铭记?”
杨桉快速地换下一张图片,“那这样,就引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尊重废墟。这是基于现状调查的得到态度,尽可能地完整保留铁轨的原貌,可是尊重之后呢?我们是否该思考怎样让它以一种新的生命力重新存在,我们该如何盘活更新,以及量化铁轨?”
随即放出三张不同的分析图,前期结束,进入正题:“首先来看交通,铁轨的部分站点还是留存,有的并入现代交通。例如三号线的火车东站旧址,整个站台完全采取原站台的装修风貌,其间的历史韵味在快节奏的都市里倍受风靡追捧,依赖于顺畅的交通,已经成为了一座市民游客都可以通达的缅怀地标。”
“其次是人居环境上,因为难以根除的历史留存问题,现存铁轨的大部分沿线,多是城中村建筑,环境、监管都属于南城城市建设的整治重点,只要是关于涉入人和铁轨的关系,难度就会成倍增加,我们该如何权衡?”
“最后是生态环境,沿途的植物多为篱笆高墙,仰仗无人打理年久失修的铁轨,植物就肆无忌惮生长越过栅栏,妄图获得更多生存地盘,而其间的动物占比高出同区数倍。这条死气横生的长路变成了南城罕见的动植物天堂,就像城市荒漠上无价的绿洲,而我们又该让他们何去何从?”
进度过半,杨桉看着沉默的台下,放出以上三张分析图叠加的整个南城铁轨原貌,主体突出了铁轨,其他部分均为灰色。
心里不自觉的吞咽,“由此,我们得出,交通作为铁轨的价值属性,率先做出的尝试,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改造铁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