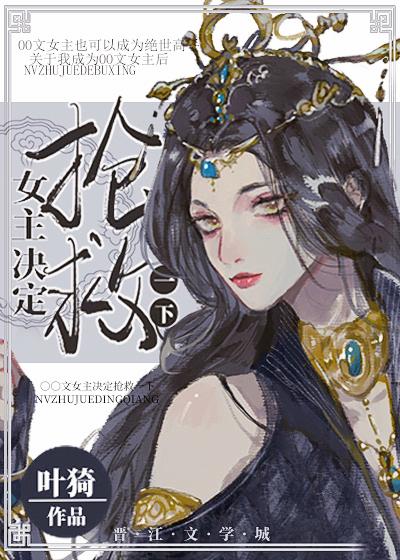02小说网>钓到漂亮奸相,但死遁了 > 修第十步试探(第2页)
修第十步试探(第2页)
即便如此,除去双亲,老师仍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人。所以在得知这次春宴老师会来,他身上毒未全解,一大早来了裴府。
*
“韩夫子?正与崔大人在前面的庭院下棋呢,您往前走便见着了。”小厮恭敬道。
庭院里已围了一圈人。沈洵舟走过去,靠边倚住栏杆,漆黑眼眸静静望着桌前对弈两人。他没说话,周围响起窃窃私语。
崔珉的棋风循循善诱,步步为营,看似温吞,实则都是陷阱。韩纪书手执白子,围剿之下,也不落下风。周遭又寂下来。
沈洵舟盯着崔珉落下黑子,轻轻皱起眉。想起那日宋萝执棋,也有一点这般诡谲的影子。
崔珉笑道:“被人盯着看,总容易出破绽,这局是您赢了。”
韩纪书这才抬眼,瞅了瞅边上的沈洵舟。一群各色晃眼的官家子弟中,青年漂亮得惹眼。两人对视,沈洵舟眉头一松,抿出一个笑。
韩纪书长叹一口气:“罢了罢了,你走吧。”
他年纪大了,不愿走动。崔珉自觉起身,颊边酒窝陷进去,温和招呼众人:“崔某听闻前方玉兰花开得正好,诸位同僚可要随某去看看?”
这是要将亭子留给师生两人,众人察言观色,立即跟着崔珉从另一边离去了。这庭院原本偏僻静谧,人走后,韩纪书拾起棋子丢入棋罐,发出清脆声响。
沈洵舟上前,乖巧帮他收拾棋盘,盖上棋罐的盖子,才喊:“老师。”
韩纪书摸了摸一旁温热的茶壶,第一句不是问好,而是训诫:“前几日有名御史,只是宴上对你出言不逊,你就逼得他辞官回乡?”
“是啊。”沈洵舟一眨不眨地盯住老师的神色,语调轻飘飘的,“老师今日是来训诫我?”
日光照入亭子,几缕金色丝线缠在他身上,脸颊惨白,唇边勾着笑。
韩纪书怒道:“我教你的仁慈之道,你都忘光了吗!”
“学生自不敢忘。”沈洵舟收回手,金线穿过眼睫,映起奇异光泽,“但这官场,又岂能容我仁慈?”
那人并非对他出言不逊,而是骂当今圣上狗眼无珠,错信奸佞,错将罪臣翻功臣。被亲中士族压下去,才保得一条命。
许久未见,他不想将气氛弄的如此剑拔弩张。
他放缓了语气:“其实缘由不止如此,我不能明说,老师的教诲,时时不敢忘,您今日来见我,就只是为了说这些吗?”
语到最后,竟有了些紧迫意味。韩纪书看着他,三年官场磨砺,到底是将当初那个柔软少年,磨得锋利如刀。
韩纪书一拍桌子,不肯承认:“谁说老夫是来见你?”
“老师年年受邀,却只有今年来了,您一贯避我如蛇蝎,如今却不绕开我,定然是来见我。”这一番话绕口,沈洵舟眸中浮上一点委屈。
“学生也许久未见您了。”他眼睫垂落,仿若仍是学宫中那个意气又爱撒娇的少年。
韩纪书看着心软,又叹一口气,拿起茶壶倒了杯茶放桌上:“行了!说这么多也不口渴,来喝茶。”
沈洵舟指尖圈起茶盏,见其中碧绿茶水轻晃,一股脑喝了。舌尖传来些苦涩,他吞咽了下,进入正题:“您若有事要我相帮,我定……”
眼前老师的脸晃了晃,他没立即说完,垂下眼,石桌上的棋盘晕成湖水,泛起圈圈涟漪。他栽倒在石椅上,浑身软绵绵的。
失去意识之前,耳边响起长长的叹息。
怎么会是,老师递来的茶呢?
*
门外的人已走了进来。
宋萝压在沈洵舟身上,呼吸不由得放轻了。好在这人从刚才便没了动静,好像死了一般,喘都不喘了。
想起自己的手还掐在他脖子上,她微微松了松,心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力道……他不会真窒息晕过去了吧?
一柜之隔。
床上的永安公主被叫醒,声音尚带着困倦,迟疑地望着一大堆人,凤眸转向最前的青年:“皇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