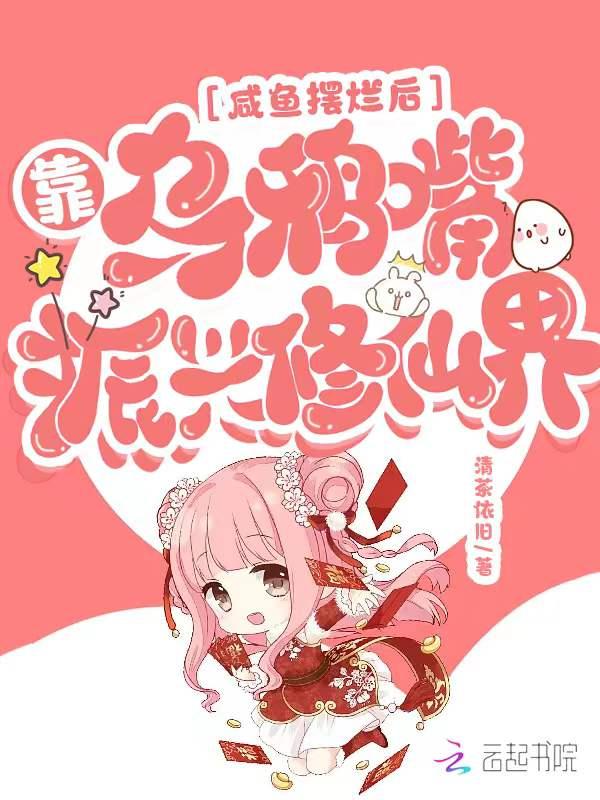02小说网>我剑悬日 > 山雨欲来风满楼(第1页)
山雨欲来风满楼(第1页)
木门吱呀轻响,殷悦抱着竹篮从院里转进来,发间沾着几片蔫掉的蔷薇花瓣,垂落的发丝遮住泛红的眼角,白裙下摆沾着新鲜泥点,像是被骤雨打弯的柔弱花枝。
她抬眼时睫毛轻颤,水杏似的眼睛蒙着层雾气,声音比蝉翼还轻:“外面…是出什么事了吗?”
时水苏上前半步,特意放缓语调:“姑娘,你可有遇见一位受伤的男子?他是我们的同门。”殷悦捏紧竹篮的手指泛白,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颤。
几个时辰前的画面在脑海闪过——浑身是血的段清淮撞开院门,在青石板上拖出蜿蜒血痕。
她抿着唇点头,侧身让出半道门槛,垂首时露出后颈一小片朱砂痣,如同一粒不小心滴落的胭脂。
祝竟遥倚在廊柱上,指尖无意识摩挲着佩剑缠绳。
看着殷悦领众人穿过爬满蔷薇的庭院,那姑娘莲步轻移,路过水缸时总要借着倒影理鬓角,发间银铃随着动作轻响。
蒋引玉却只顾低头观察祝竟遥的伤口,粗粝的手指捏着布条格外小心;谢有仪抱着剑,连个眼神都没分给殷悦;最年轻的松芮佳倒是好奇地打量四周,也只是礼貌地说了句“叨扰”。
往后几日,小院里总飘着草药香。殷悦每日寅时便提着竹篮出门,归来时裙摆沾满晨露,发间插着带露的芍药。
她将花瓣细细撕碎,混在药汤里熬出甜香,瓷碗边沿还总要摆片薄荷叶。
时水苏坐在石桌边与她闲话,时而指着远山询问山势,时而展开泛黄的药草图卷,教她辨认止血的紫珠草。
殷悦学得认真,只是总在低头记录时,偷偷往段清淮房间的方向瞥上一眼。
祝竟遥常坐在屋檐上晒太阳,抱着酒葫芦晃悠。有次正巧看见殷悦端着桂花糕,猫着腰往段清淮房间去,发间珍珠步摇随着动作轻晃。
刚到门口就撞见蒋引玉端着药碗出来,两人同时愣住,殷悦慌乱后退半步,糕点上的糖霜簌簌掉落。
蒋引玉挠挠头,把药碗往她手里一塞:“姑娘受累,劳烦再劝劝他喝药。”
祝竟遥仰头灌酒,无声笑出了泪花,酒液顺着嘴角滑落,在衣襟上晕开深色痕迹。
第五日晌午,屋里突然传来瓷器碎裂声。祝竟遥翻身落地,佩剑出鞘半截,就看见段清淮抓着窗框要往外爬,绷带散了半截,露出结痂的伤口。
殷悦举着药碗站在床边,泪珠在眼眶里打转:“段公子,你的伤口…”
话音未落,祝竟遥已倚着门框轻笑,身后蒋引玉等人齐刷刷现身,松芮佳还晃了晃手里的缚仙索。
段清淮僵在原地,额角青筋跳动。他正要运功突破,却在转头时撞见殷悦蹲在地上收拾碎片,指尖被瓷片划出细痕也浑然不觉。
恍惚间,昏迷时那些模糊的片段突然清晰起来——总感觉有双温柔的手替他擦汗,有个软糯的声音哼着不知名的小调,药汤里还混着若有若无的花香。
他看向祝竟遥满脸假笑的模样,也知道了祝竟遥如今还不想与他撕破脸皮,性命之虞暂时无了。
此后的日子,小院愈发热闹。清晨总能听见段清淮练剑的破空声,殷悦就躲在厨房门后偷看,被发现时慌忙转身,却碰倒了墙角的陶罐。
段清淮教她辨认灵草,两人的指尖总在递接叶片时不经意相触,殷悦便红着脸往后退,发间银铃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祝竟遥抱着酒坛蹲在墙根,看着段清淮手把手教殷悦搭晾药草的架子。
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渐渐重叠在一起。
她仰头灌了口酒,忽然觉得天道给的惩罚也没那么难捱。至少,她亲眼看着原著剧情,像春日里的残雪,在她眼前化得一干二净。
夜里,殷悦端着新熬的莲子羹轻手轻脚走进客房。段清淮正对着窗棂发呆,月光洒在他削瘦的侧脸上。
“段公子,这是安神的…”殷悦话没说完,段清淮突然转身,目光灼灼:“为何对我这么好?”
殷悦慌乱间打翻了羹汤,瓷勺在青石砖上敲出清脆声响,溅起的汤汁在月光下泛着微光。
祝竟遥倚在隔壁窗边,听着墙那边传来的动静,嘴角勾起一抹笑。
远处传来更夫打更声,她摸出怀里的玉心莲,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这几日她暗中尝试,发现噬魂术与玉心莲共鸣时,体内的天道烙印会泛起细微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