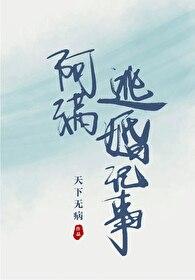02小说网>表小姐今天也在装老实 > 哄她(第3页)
哄她(第3页)
余晚萧自去换衣,卸下骑装,换上原身衣物。然她翻检之时,却发现最外层的坎肩不见了。
书苑衣衫本有多层,天热时可减,天凉时便添。昨夜落雨,今日天气微凉,故余晚萧晨起时便加了这坎肩,此刻却不知去向。
她仔细寻了几遍,仍不见踪迹,当即去问守在院门口的女兵,方才此间屋舍可有他人来过。
女兵回禀:“来过几人,却皆是女眷。”
许是谁不慎拿错了。好在这是文澜书苑的制式坎肩,学子人手一件,丢了也无大碍。若是里衣遗失,那才是桩麻烦,这世道,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最怕有心人拿此事做文章。
余晚萧这般自我宽解,只想着日后手头宽裕了,再去添置一套书苑服饰便是。换妥衣裳,便安坐等候越莺归来。
………
七月初七乃七夕佳节,文澜书苑给众学子放了一日假。
陈必得又要办诗会,二房人皆需到场,他却特意给了余晚萧些银子,让她自去街上逛逛。大约是上次诗会,余晚萧那句即兴诗作让他失了颜面,此番便不愿再让她参与。
余晚萧面上露出几分失落,陈必得见状,又多给了几两银子打发她。殊不知她本就打算出门,这般一来,反倒平白得了些银钱。
这节日里,街上男男女女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制巧果、染指甲、拜七姐、放花灯等诸般活动层出不穷,满眼皆是恩爱缠绵的身影。
松风阁二楼,赵长亭斜倚栏杆,百无聊赖地望着楼下二人。他们自以为举止隐秘,却不知赵长亭早已观察了许久。
越莺今日穿了件粉色衣裳,还细细描了眉。她本就生得冰肌玉骨,容貌艳丽,经这一番打扮,更显风华绝代。方才已有好几个路过的男子想上前搭话,都被梁恕拦了回去。
越莺忐忑地瞟了瞟梁恕,轻声道:“宥之哥哥,你把手摊开,我给你个物件。”
梁恕眸光温煦,依言摊开手掌。只见她取出一个香囊,上面针脚歪歪扭扭,绣的纹样也辨不清是何物,香囊被捏得皱皱巴巴的。
男女之间互赠香囊,其意自明,乃是心悦之证。
就在那香囊即将递到手中时,梁恕却收回了手,郑重道:“这不合宜。”
越莺却不以为意:“有何不合宜?莫不是你瞧不上我的香囊?”
梁恕放低了声音,循循善诱:“你可知男女之间赠送香囊是何意?”
越莺仰起头,目光热切,正如她的性子一般,永远这般热烈明媚:“我自然知晓,不然怎会送你这个!”
梁恕眼中藏着克制与隐忍,无奈轻叹:“雀儿,你将这话收回去,我便当从未听过。”
“雀儿”是越莺的小名。她幼时久居宫中,日子清苦,如履薄冰,总盼着能化作雀鸟,飞出那高耸红墙,故自取此名。除了亲近之人,再无人这般唤她。
“我不!这香囊我偏要给你!”越莺固执地将香囊系在他腰间,抱臂嗔道:“不许取下,否则我便恼了。”
梁恕对她无可奈何。见她这般执拗,到了嘴边的规劝尽数咽了回去。即便是好言相劝,越莺也断不会听进去半句话,她本就是那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性子。
罢了,家中已在为他议亲,待亲事定下那日,想来越莺自会歇了这份心思。
二楼的赵长亭嗤笑一声,不以为然。人生在世,本就该今朝有酒今朝醉,他这友人偏是顾忌太多,才活得如此束手束脚。
梁恕闻声抬头,见他竟在一旁窥看,不悦地唤道:“长亭!”
赵长亭嬉皮笑脸道:“我什么也没听见!”
嘶~这话怎的如此耳熟?
他的脑中不由自主浮现出余晚萧说这话时的模样,那副无辜诚挚的神情,说得跟真事一般!
他失笑摇头,收回视线,拿起手边的《风月录》翻看。
那日他心浮气躁,去了舞坊寻那舞西施。那女子身段妖娆,眉眼勾人,他却只觉索然无味,最终还是打道回府,靠着这《风月录》饮鸩止渴。
可这书,他早已翻来覆去看了不知多少遍,里面的字句都能背得滚瓜烂熟。这出书之人,怎的还不见第二册问世?
真真叫人盼得肝肠寸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