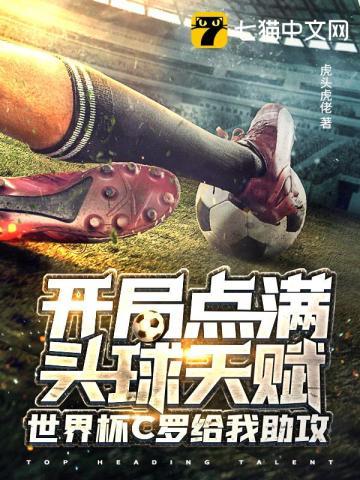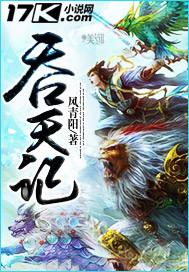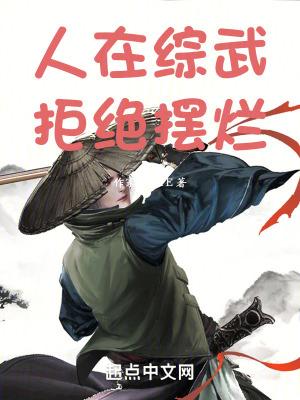02小说网>炽年长明 > 裂隙(第2页)
裂隙(第2页)
黎予发来早餐照片:一碗撒着葱花的清汤面。平时她会回“看起来很好吃”,但此刻,她盯着屏幕,手指悬在键盘上,大脑却一片空白。
不是不想回,是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每一个简单的回应都变得无比艰难,仿佛要用尽全身力气。
最后她只回了一个:
『嗯』
发送成功后,她像完成了一项艰巨任务,长长舒了口气,同时涌起一阵强烈的自我厌恶。
又过了些时日——也许是两天,也许是一周,她对时间的感知越来越模糊——
她发现自己对黎予发来的消息产生了恐惧。
手机提示音响起时,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期待,而是心悸。
那种感觉像是被推上一个舞台,却忘了所有台词。她开始拖延回复,从几分钟到几小时,再到一整天。
“我在看书,等下回。”
“在吃饭,晚点说。”
这些借口连她自己都说服不了。
更可怕的是,她发现自己正在失去感受能力。黎予分享的趣事不再让她发笑,关心的问候不再让她温暖。一切都隔着一层毛玻璃,模糊而遥远。
某个分不清是下午还是黄昏的时刻,她蜷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已经很久。母亲进来问她晚上想吃什么,她连摇头的力气都没有。
手机在地毯上震动了一下。她用尽力气伸手拿过来,是黎予的消息:
『今天下雨了,你那边冷吗?记得加件衣服』
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理智上知道这是关心,但情感上却是一片荒漠。
她甚至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如果没有我,黎予会不会更轻松?
这个想法让她浑身发冷。
从某个记不清的日子起,她开始回避一切需要情感投入的互动。黎予发来的长消息,她只看前几句就划掉
这不是讨厌,不是不爱,而是情感系统的瘫痪。就像断电的机器,再精密的程序也无法运行。
直到又一个模糊了晨昏的日子,她看着黎予接连发来的消息,感觉自己像被逼到悬崖边。每一句关心都变成沉重的负担,每一个问号都像是在质问。
语音通话的请求在屏幕上闪烁了一会儿,最终因无人接听而自动挂断。
耿星语蜷在窗边的单人沙发上,看着手机屏幕暗下去,像完成了一个艰难的任务般松了口气。
这不知是黎予今天发来的第几条消息,她一条都没回。
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那种强烈的、想要把自己藏起来的冲动又出现了。就像退潮时被独自留在沙滩上的贝壳,她渴望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不需要回应任何期待,不需要维持任何表情。
黎予是那么地体贴,可这份体贴此刻却像另一重压力,让她更加自责——
明明对方这么好,自己为什么就是提不起精神来回应?
她把手机调成静音,屏幕朝下扣在桌上。这个动作像是在完成某个仪式,宣告着她要与外界暂时断绝联系。
时间无声流淌,她维持着同一个姿势,几乎没怎么移动。思绪像被困在漩涡里,不断下沉。那些熟悉的自我质疑又开始在脑海中盘旋:
“你这样冷漠,会伤害到她。”
“她迟早会受不了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