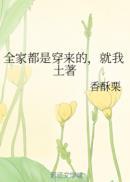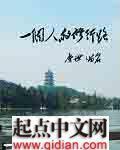02小说网>本王的科技树长歪了 > 战火淬炼(第1页)
战火淬炼(第1页)
边境的烽火如同一声急促的号角,瞬间打破了汴京的平静,也将赵楷和他的“标准化”工坊卷入了真正的风暴中心。军令如山,枢密院的文书措辞严厉,要求将作监不惜一切代价,在最短时间内,向前线输送最大数量的合格箭矢和弩机备件。
压力如同实质的山峦,轰然压在了赵楷的肩头。这不再是演习,不再是观摩,而是实战!前线的将士在浴血奋战,每一支箭,每一个弩机零件,都可能关系到一条性命,一场战斗的胜负!
工坊内,气氛凝重到了极点。所有与军械生产无关的项目全部暂停,人手被紧急调配,炉火日夜不息,敲打声、锯木声、号子声汇成一片,空气中弥漫着焦灼和铁腥味。
赵楷站在工坊中央,嘶哑着嗓子下达指令,眼睛布满血丝。他知道,这是检验“标准化”成色的最佳时机,也是最为残酷的考场。
“所有工位!按规程操作!质检员就位!每一批零件,必须过检!不合格的,立刻回炉!绝不允许一件次品流出!”他反复强调,声音因过度疲劳而颤抖。
关键时刻,“标准化”的优势开始显现!
由于之前推行了统一的图纸、量规和工艺流程,工匠们(尤其是新招募的临时工)上手极快,减少了大量的摸索和试错时间。流水线式的作业模式(雏形)也初显威力,各司其职,效率远超以往混乱的各自为战。
质检环节更是发挥了巨大作用。尽管老师傅们依旧抱怨“束手束脚”,但在赵楷的强令和战争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他们不得不按照标准检验。简易的极限量规、卡板被大量使用,虽然粗糙,却有效筛掉了一批尺寸偏差过大、存在明显缺陷的零件,避免了后续组装的无用功和战场上的潜在风险。
“快!三号工位箭镞毛刺超标!退回重磨!”
“七号工位弩机钩心硬度不足!整批报废!”
“装配组注意!三号轴与五号孔配合过紧,使用备用件替换!”
质检员的呼喊声此起彼伏,虽然导致了一定的废品率和短暂延误,却保证了最终产品的基本合格率。
然而,问题依旧层出不穷。
最大的瓶颈依旧是材料。紧急状态下,库房拨付的铁料、木材质量参差不齐,杂质多,性能不稳定,极大影响了加工效率和零件质量。赵楷急得跳脚,却无能为力,只能要求工匠加强筛选和检验。
人员疲劳也是大问题。日夜赶工,工匠们疲惫不堪,失误率开始上升。赵楷不得不将人手分成两班,轮流休息,并自掏腰包(狄明月赞助)购买肉食,给大家补充体力,但效果有限。
工部派来的“观察员”钱主事,此刻也不再冷嘲热讽,而是阴沉着脸,带着人四处巡视,拿着小本子记录着什么,显然是在寻找差错,准备秋后算账。
张匠头等人虽然也在拼命干活,但眼神复杂,似乎既希望完成任务,又暗暗期待着赵楷出错。
压力、疲劳、监视、潜在的危险……工坊如同一个高速运转却充满隐患的机器。
就在这紧张到极点的时刻,一个噩耗传来——一批即将发往前线的“靖虏弩”备用弩臂,在最后抽检时,被发现有细微裂纹!
“怎么回事?!”赵楷冲到库房,看着那几十根几乎看不出问题的弩臂,头皮发麻。
负责检验的老工匠脸色惨白:“回……回先生,是……是木料的问题!这批硬木送来时就有些暗裂,烘干时没彻底……加上最近天气返潮……应力释放……就……”
赵楷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弩臂有裂纹,上了战场就是炸膛的结局!非但杀不了敌,还会伤及己方士兵!
“全部扣下!一根不准发!”赵楷嘶声吼道,心脏狂跳。
“可……可前线急等……”孙主事急得团团转。
“等也不能送!”赵楷斩钉截铁,“这是害人性命!立刻排查所有同批木料制作的部件!快!”
工坊内一片混乱,气氛降到了冰点。
钱主事闻讯赶来,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赵先生,这就是你推崇的‘标准化’?连材料都把控不住,出了如此纰漏!延误军机,该当何罪?!”
赵楷没时间跟他废话,红着眼睛吼道:“材料是库房送的!检验规程有漏洞,是我的责任!但现在首要任务是补救!铁蛋!带人立刻去库房,检查所有同批次木料!小鱼!带人连夜赶工,重制弩臂!所有人工钱加倍!”
他强行压下恐慌,指挥若定。关键时刻,他不能乱。
工匠们看着赵楷扛下责任,并迅速组织补救,慌乱的情绪稍稍稳定,重新投入工作。
经过彻夜不眠的排查和抢工,受损的弩臂终于被更换,危机暂时解除。但延误的一天时间,却无法追回。
赵楷心力交瘁,却不敢有丝毫松懈。他意识到,“标准化”绝非万能。它可以在工艺和流程上提升效率和一致性,但却无法解决源头材料和人为因素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战后,必须推动材料标准化和更严格的质量追溯体系!他在心中暗暗发誓。
就在工坊上下拼命赶工之时,前线的战报陆续传回。
一开始多是坏消息:堡寨被围,伤亡惨重,箭矢消耗巨大……
但随着补给车队将第一批紧急生产的箭矢和零件送抵前线,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出现。
数日后,一份来自前线的特殊文书被快马加鞭送到了枢密院,又由曹玮的亲随紧急送到了将作监工坊。
当时赵楷正满身油污地蹲在炉前,亲自盯着一批急用的弩机钩心淬火。亲随找到他,递上一份密封的信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