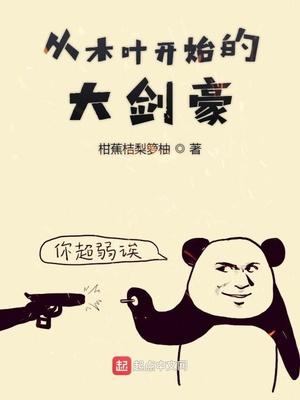02小说网>燎传 > 医者3青青丹药(第2页)
医者3青青丹药(第2页)
“大父,若是如此,那岂不是救一人,医一半?”
孙奂望着案上的草药道:“姜儿,你天性善良,大父所想你或许难以明白。”
无姜问:“大父所谓是何事?”
孙奂拨弄着草药道:“姜儿,凭大父半生阅历,乐正此人未必恶徒。但是我看他伤势,非一般武者可伤。习武之人,这内家功夫练到像他这样的地步,一般武夫也难以把他伤成那样。”
无姜道:“大父可是说,像乐正这样的高手尚且被打成重伤,那他的仇家的功夫就比他更加厉害?”
孙奂碾碎半夏和瓜蒌仁,他道:“他左腋重伤,内气冲身。左手臂结实宽厚。乐正应该是左手使兵刃的江湖中人。他腋下
之伤一直延伸到臂膀,若是那攻击之人再朝他左臂膀斜削上去,半条臂膀尽废无疑。”
无姜现在听明白了,她道:“那仇家把他打成重伤,不仅要废了他臂膀,还打入真气压他内功?”
无姜虽然不懂武学,但是她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她继续道:“大父,你平日说习武之人以内劲催动功力。乐正手臂与胸腔皆受伤,再加体内真气冲击,如此情形,那便是用不上兵刃,使不出功夫了?”
孙奂道:“正是这样。昨日我听巡查的兵士说,这人在吴县游荡多日。我估他是和仇家械斗败北,带着重伤流落至此地。或许是仗着自己内功深厚,这样捱了一日便是一日。”
无姜听祖父这么一说,忽然心中升起一股恻隐之心。她轻轻道:“这么看,乐大哥也真是可怜。”
孙奂道:“此人的仇家,武功远在他之上。我想这小子心中肯定一直存着报仇的念头。方才我还道他惹上江湖仇杀。以眼下而论,他涉足江湖之事十之八九。但于我而言,他现在只是一个暂时失去武功的病人。我医他治他,权且算作路边的困顿游民。现在治好他,只是把他的身子养好。治他内伤一事,则属于江湖纷争。大父绝不参与,否则就有违我先
前之誓。”
无姜听罢,她内心纠结。无姜知道祖父曾立下誓言不再以医术施救江湖中人,以免自己再次卷入江湖之事。先前她听到祖父要给嬴栎刮骨疗伤之后,确是非常担心祖父涉险。但是无姜毕竟医者仁心,换做她来救治嬴栎的话,也自当义不容辞。
孙奂将调和的草药分在两个陶碗里,他接着道:“昨日载他回来之时,这小子还说要去太伯神社拿一件东西。我说你伤势沉重,不宜行动。但是他反复求我带他过去,说是这件东西对他来讲非常重要。”
无姜问道:“大父可知道是何物?”
孙奂摇头道:“不知。他也没告诉我是何物。”
“那大父可要让他去取物件?”
孙奂点点头:“他既然把那物件看的如此重要,想必是贴身信物。也许县上寻常百姓见了他只道是落魄乞丐,但是我想他流落至此定然有什么事情要办。”
无姜道:“大父,若是可以,待他醒了我们问问他身世可好?”
孙奂点头道:“正有此意。他的伤势一时半会儿不能痊愈。这小子啊,要在我们家待上些时日了。”
孙奂把陶碗拿在手里,他对无姜道:“姜儿,今夜你也累了。这快到丑时了,你也没好好休息,回屋歇会儿。”
无姜道:“那大父呢?”
孙奂笑了笑:“我去大屋里看看那小子,待到鸡鸣了再收拾收拾。”
“大父也多当心身子。姜儿就先回屋了。”
孙奂收好药材,无姜替他吹熄蜡烛。祖孙两人出了药屋,无姜又和祖父叮嘱了几句。便回屋休息去了。
孙奂呆在大屋里,他见嬴栎气脉逐渐平稳,知他风寒发热正在消去。他又试了试嬴栎内力,此时嬴栎体内虽仍有真气躁动之状,但相比一开始已经算是好多。孙奂放好青栀丸粉。从角落中取出一个大大的竹制书箱,这书箱里面有数卷清白干燥的竹简放置着。
孙奂取出一支书刀,在大屋隔间的烛火下刻起字来。孙奂这一刻,一直坐到第二日旭日方升。
那边嬴栎睡了多个时辰,待他再次醒来时以近午日。嬴栎睁开双眼,只觉得脑海一沉,他定了定心神,轻轻挪动了一下受伤的左臂。嬴栎发觉现在左臂可以挪动,他移了移身子,右手使出力气撑住床褥,这次终于算是能够坐起来了。
嬴栎喘了口气,他打量了一番四周环境,只见这件石屋的四墙之上都挂着些蓑衣镰刀等物什;而在各个墙角处又放置着几个三层左右高的木制架子,上面摆满了干燥的药材。整个屋室里弥漫着草药的清香,嬴栎嗅了只觉得胸中舒坦,先前的积郁随着草药的芬芳灌入而一扫而空。
嬴栎又看了看身边的床褥,只见床沿一边还留着深色的血迹,他摸了摸伤口,发现伤口已经被细致地包上了麻布绷带。绷带包扎得甚是服帖,嬴栎感觉不到之前疮口的肿胀感,想是孙奂给自己的疮口去腐处理,治疗了外伤。
嬴栎想下地走动,他掀开被褥,这才发现自己赤裸着半身。嬴栎四处搜寻自己的那件破衣,却发现不见踪迹。他又张望了一阵,这才看到床榻边的案上放着一套叠好的棕青布袍。嬴栎猜想是那对祖孙留下的,他接过布袍,看到这袍子虽然陈旧打着补丁,但是浆洗地甚是干净。嬴栎把袍子穿在身上,一股更加浓烈的草药味冲鼻入肺。较之这屋里的清香,这袍子上的气味倒是更加刺鼻激烈。
嬴栎盘腿坐在床上运功调息,他脑海中仔细回想了一下《归藏》之上的内劲吐纳之法。练了一会儿,嬴栎只觉得丹田中一股热气上涌,但是这股内劲来到心脉周边时又被另一股更加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