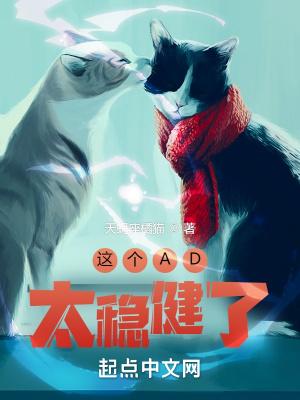02小说网>初唐异案 > 283 落日余晖(第2页)
283 落日余晖(第2页)
“圣人天尊,还望请息怒……”内侍因害怕而哀求的告饶声此起彼伏。
圣人罕见地青筋暴起,瞳仁瞪出,看向婉儿,“何人,汝与朕言,究竟何人这般欺公罔法,以私刑支解前平阳王,连朕亦分毫不知,岂非不怕灭九族的罪过!”
听得此一句,婉儿念及每每圣人于朝堂之中的表现,自己表现得反较初至之时,更为平静,甚有些淡然地回答,“乃中书舍人,周利贞授意,再由当地州官领武侯亲行。”
“周……”圣人才听到周利贞的名字,便顿时哑然失言。
彼时异骨案结,又逢还都
长安,故而周利贞请缨“安置”获罪五王时,圣人亲口交代若流放途中或流放至在地,凡口含不忿之言,或颇有微词之人,无论五王、沿途官员百姓,皆由周利贞自行定夺,不必上报复议。
而至为致命的一道口谕,便是自行判断,若五王有不察之举动,亦可直接制止,而不必复议。
想来,便是此一句,如今将流放至琼州的敬晖置于死地。
“实乃朕怒火未消……所犯何罪,却又怎至将他支解……”
见圣人对此事尚有悔意,而又不愿亲自览阅奏书,婉儿将奏书拾起,开始逐字逐句轻声念起。
那日,敬晖满腔欣喜,行至官衙门前,聚于彼处的并非只有每每有官差至,便会到齐的各级官员以及兵士、武侯,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百姓,人人看向敬晖自身的眼神,都似与寻常不同。
猜测状况不妙,敬晖只得先行问道,“可是有何事要寻敬某?”
一名贼头鼠目、两颊胡须细长的官差模样之人从人群中走出,略有些嬉笑,“寻敬公者,正是在下,此番有一字,在下由人所托,特为敬公带来……”
听闻这一句,敬晖才知先前小儿所言“领字”,确是如听来之意,此时还不忘看向方才领他至此处的几名小儿,微微点头。
“敢问官家,是为何字?又有何人所托,只为将一字送至此处?”
“敬公有礼,如何望敬公唤在下区区一名内仆为‘官家’
,平阳王折煞在下了!”
“敬某已然被贬谪于此琼州,无官无职,仅为一为官府书写、拾遗之庶人,还请官家,先行将字展于敬某一观,何如?”
敬晖说罢,只见对方胡须上扬,将封好的一份书信递于他手,查看信封,才见上书一字“源”。
“此封书信可是来自东都源府?”
“在下不知,只是有他者将此信交于吾手,托在下转交。”
这番表现,让敬晖不由半信半疑起来,在当场众人注视下,他撕开信封,缓缓展开信纸,有些昏花的眼睛,随着字里行间逐渐撑开眼眶。
书信中所述,乃是长安僵血案中,敬府险为回鹘一众屠虐,此外还有眼下仍未得有确切说法之东都鳞症案,其中提及的乃是敬晖甚为宠爱之源阳、源协二人,已然因于异案有嫌,被投入大狱之中。
“敬公以为何如?”
“吾儿家中蒙难,是为冤;东都源府乃吾敬氏一族,素来交好之望族,竟无故卷入未知异案,且甚因此入狱,更为冤,如官家尚可向上进言,还请行劝言……”
“敬公暂且收心,莫要关注他人,”对方这名内仆忽而换了副面孔,“敬公怎未察僵血案,回鹘祸乱长安,偏要灭尽敬府,岂非之中尚有不可名状之事,据在下所知,敬公彼时于东都集结隐兵,可是误伤、误杀百姓诸多,其中难免有回鹘而来,如此莫非是为寻仇?”
“而与敬公交好之源府,
其一子一女如今卷入新件异案,更是被疑为主谋,若只以在下浅见,先是被贬谪之五王,后又是前中书侍中源乾煜之源府,如何不得猜疑与敬公相连之一众,即天然期望大唐为乱?”
此人言语一处,四周窸窣议论声四起,显然“误伤、误杀百姓诸多”一句,让本以为敬晖良善的住民,亦感担忧。
自东都异骨案结始,敬晖便一直活在各种猜忌之下,无论圣人、还是复周一派,甚至于其中一段家人也对自己所作所为不解,终于各种闷于心口之怨气,在此一刻释放。
他仰天大笑道,“李哲小儿!我五人予你大唐疆土,尔这奴便是是这般对待于开朝老臣!?如此便是敬某入了地狱之下,见得武后、高宗,也要因尔好好论教一番……”
敬晖不断叫骂,发丝须髯尽乱,表现亦与发狂无异,口中言语对李唐皇族极尽辱骂,直至被武侯将他的脸直直按入土中还不止。
在还能略微抬眼看看四周时,敬晖再瞥了一眼才东升不多时,还未至中天的太阳。
心中不免将牵挂之人的面庞再度回想了一轮,像在对他们言说,又像自言自语,“今日稍晚时之落日,便是老朽得见之最后一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