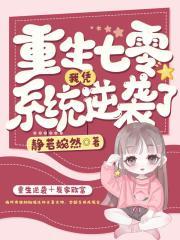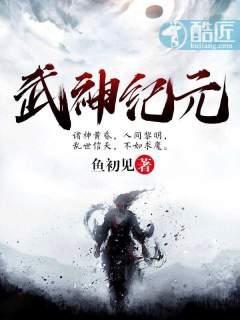02小说网>大国军垦 > 第3090章 叶帅回国(第2页)
第3090章 叶帅回国(第2页)
叶帅想起临走前父亲塞给他的小布袋,里面装着五种麦种,标签上写着“戈壁1号”到“戈壁5号”。
父亲当时说:“别觉得种子只是种子,它是能跨山越海的信使。”
第二天去别尔哥罗德的路上,司机忽然拐进条小路。车窗外出现一片试验田,田埂上插着五颜六色的牌子。
红牌写着“华夏北疆”,蓝牌写着“乌克兰吉普”,黄牌写着“联合培育”。
农业局的局长早已在田边等候,指着田里的麦苗说:
“您看,这是用您父亲的麦种和本地品种杂交的,抗寒又抗旱。”
叶帅蹲下来,指尖拂过麦叶上的绒毛。阳光透过叶尖的露珠,在泥土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极了沙漠光伏板反射的光点。
局长忽然递来份协议:“我们想建个光伏灌溉示范区,就用你们的‘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模式。”
他指着远处的山坡,“那里规划了五千亩地,一半种麦子,一半种苜蓿,苜蓿用来养牛,牛粪还田,形成循环。”
叶帅看着协议上的签字栏,忽然想起库尔班老爷子给的那颗糜子种。
他来吉普前,把它种在了军垦城的实验室,此刻大概已经发芽了。
他在协议上签下名字,局长笑着说:
,!
“下个月中乌农业论坛,您得做个报告。很多农庄主都想知道,怎么让土地既长粮食,又长‘金子’。”
晚上住在试验站的宿舍,叶帅打开父亲给的布袋。
五种麦种躺在掌心,像五颗小小的星星。他忽然明白母亲为什么要他回来——军垦城的种子在吉普扎了根,现在需要有人让它长出新的枝芽。
半个月后,叶帅在农业论坛上展示光伏治沙的成果时,台下忽然有人举手:
“华夏的技术很好,但我们的黑土和你们的沙漠不一样,能适用吗?”
叶帅笑着点开一张图片:屏幕上,别尔哥罗德的黑土地上,光伏板下的麦苗正抽出新穗,旁边的对比图里,是xj沙漠里的同款光伏阵列。
“土地不管是黑是黄,都需要人懂它。”他说,“沙漠要防沙,黑土要保肥,道理是一样的。”
论坛结束后,伊万诺维奇打来电话:
“你母亲把军垦连锁超市的股份又转让了一部分,说要给你建实验室。”
叶帅刚想说不用,舅舅又说,“别拒绝,这是她当年在吉普许下的愿——让华夏的种子在乌克兰生根发芽。”
叶帅站在试验站的了望塔上,望着远处连绵的麦田。夕阳把光伏板照得像铺了层金箔,板下的滴灌带正滋滋地往土里渗水,那声音和沙漠里的滴灌声一模一样。
他掏出手机,给父亲发了张照片:黑土地上的光伏阵列,像片蓝色的湖,湖边的木牌上,新刻了行字:
“让每一寸土地都长出希望”。
手机很快震动起来,是父亲的回信,附带一张图片——军垦城的实验室里,那颗糜子种发了芽,嫩绿的茎秆上顶着两片子叶,像个小小的“v”字。
父亲在信息里说:“你姥爷说得对,土地不会辜负认真耕种的人。”
叶帅望着天边的晚霞,忽然觉得,所谓传承,就是一粒种子从北疆沙漠到乌克兰黑土的旅程。
它会带着沙漠的坚韧、黑土的厚重,在风里生根,在雨里发芽,最后长成连接两片土地的桥。
就像父亲当年带着麦种跨越国界,就像他此刻站在这片黑土地上,手里握着来自故乡的种子。
风从麦田里吹过,带着麦香和泥土的气息。
叶帅知道,这里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就像沙漠里的红柳总要把根扎进深处,他的根,一端连着军垦城的试验田,一端系着吉普的黑土地,而中间,是无数正在发芽的希望。
叶帅在别尔哥罗德的第三个月,迎来了第一场雪。
试验站的光伏板上积了层薄雪,阳光一照,反射出的光晃得人睁不开眼。
他踩着没过脚踝的雪,查看埋在地下的温控设备——这是从军垦城引进的技术,能让土壤温度保持在5c以上,确保麦苗在寒冬里也能缓慢生长。
“叶顾问,伊万诺维奇副部长来了。”
农业局的技术员小跑着过来,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成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