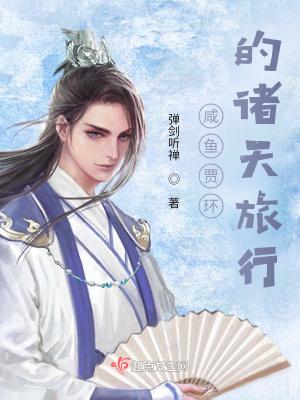02小说网>港片宇宙之靓坤 > 第332章 星星知我心(第2页)
第332章 星星知我心(第2页)
虽然没有达到“割席”的地步,但是见面之后的笑容里有那么一丝尴尬。
……
不上补习班的时候,沈佳宜放学后会留在教室学习到差不多的时间再回家。
等沈佳宜穿过操场的时候,就是一群人回家的时候,走在沈佳宜身边的,总是靓坤。
其他满心嫉妒的男生,会用搞怪的表情和语气说:“你们在谈恋爱哦!”
喘气如牛的呼兰曾经说过这么一个小段子:“小学的时候,男孩子喜欢一个女孩子,他就传女孩子和另外一个男孩子的绯闻,传着传着就成真的了。(传绯闻的男孩子)你图啥呢?”
亚洲舞王尼古拉斯·赵四的亲家刘能说过:“大人干不出来这事!”
……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又是一年。
在1976年2月14日情人节那天,同时也是元宵节。
在弯弯的掩护下,沈佳宜和靓坤两个人开始了一整天的游玩。
前清时的台湾元宵还大抵和中原节日习俗相彷佛,但到了胡建伟修《澎湖纪略》时(1759年),已可看出台湾的地方特色逐渐形成:各庙中张灯,男女出游,谓之看灯。庙中扎有花卉人物,男妇有求嗣者,在神前祈杯,求得花一枝或“亚公仔”一个,回家供奉,如添丁,到明年元宵时,另做新鲜花卉、人物以酬谢焉。
是夜,男女出游,以窃得物件为吉兆。未字之女,必偷他人的葱菜。谚云:偷得葱,嫁好公;偷得菜,嫁好婿。未配之男,窃取他家墙头老古石。谚云:偷老古,得好妇。又妇人窃得别人喂猪盆,被人咒骂,则为生男之兆,周年吉庆云。
元宵夜的偷俗,在铃木清一郎的《台湾旧惯婚葬祭年中行事》(1934年)中都还有相同的习俗。只不过据铃木的记载,所偷拔的菜不拿回家,必须放置原处。欲求子的妇女则偷拔人家的竹篱以为吉兆,因“竹篱”谐音台语的“得儿”。
另一种元宵乞子的习俗则是“贯灯脚”,据说欲求子的妇女从灯下穿过就可望生男孩。
正月十五还有“听香”的风俗。听香的方法是,先在神前烧香掷筊。请示过出行的方向后,于途中窃听他人谈话,再根据所听的容,向神前掷筊占卜今年的吉凶。
许多寺庙,也在元宵节举行“乞龟”的活动,以作为庆祝。所谓“乞龟”,就是由庙方准备由糯米或面粉制成乌龟摆在庙前。元宵节当天可由信徒掷筊乞回,让家人“吃平安”。乞得面龟的人家,明年元宵必须还给庙方一个更大的面龟。于是,面龟每年愈作愈大,甚至有重达数百台斤的。至于前年乞龟后,到今年尚未还愿的,庙方都会将他们的姓名公布在墙上,俗话说『龟爬上壁』。当事人往往会成为众人戏谑的对象。
相对于“乞龟”,客家人还有在元宵节“赛新丁粄(粿)”的风俗。每年元宵节,角头内新添丁的人家都制作相当数量的新丁粄分赠每户人家。另外,再做一个巨大的粄放在庙前的广场。
另外,客家人中也盛行上元节“掷炮城”的活动。炮城是在广场上竖起一根高度可自由调整的竹竿,上端置一方形桶,四周钻孔,内置一小串连炮。参加射城的人,将点燃的爆竹丢向炮城,如果桶内的连炮被引燃了,就算是胜利,可向主办单位领取奖品。
祭玄坛爷也是台湾元宵特有的风俗。玄坛爷也称玄坛元帅、寒单爷。传说即商朝的武官赵公明,因善于理财而致富,民间奉为武财神。祭祀玄坛爷的神像绑在竹竿上,由四名赤膞的大汉扛着前进。据说玄坛爷怕冷,所以民众便掷鞭炮为祂驱寒。一般相信,鞭炮炸得愈旺,当年的财运也愈旺。所以,神轿所之处,往往成为鞭炮射击的对象,抬轿的乩童也被炸得皮开肉绽。
类似“炸玄坛爷”而规模更盛大的,则是名闻中外的台南盐水蜂炮。据说在光绪初年,盐水一带瘟疫肆虐,居民便请关圣帝君出巡遶境;以驱逐邪疫,为了助关公的气势,沿途便大放炮竹烟火,没想到瘟疫果然就此此绝迹。从此,每年关公出巡时,当地人都竞放鞭炮以答谢神恩。如果有人要向关公还愿,还会准备巨大的炮城,上面插满了数万枝的蜂炮。等神轿一走到面前就马上点燃,顷刻之间,上万枝蜂炮如万箭齐发,咻咻地向人群射去,硝烟弥漫之中,只见火花响炮到处乱窜,人群惊叫走避。就是这种叫人又爱又怕的蜂炮,每年吸引了数万人涌进盐水小镇,成为南台湾着名的元宵活动。
所谓“南蜂炮、北天灯”,台北的平溪、十分一带,则有元宵节放天灯的习俗。
天灯又称孔明灯,据是诸葛亮发明来作事信用的。另一说则以为天灯的外型和画像中孔明的帽子很相似,因而得名。天灯是运用热气上升的原理使整个灯飘上天去。平溪、十分虽然地处偏远山区,但是放天灯的习俗经过报导后,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往参观。有“放得越高,事业做得越旺”的说法。
平溪就是靓坤和沈佳宜的目的地。
从艋舺出发,到木栅,在木栅动物园(与真实情况不符,但是不要在意这些细节)看过那头著名的大象林旺之后,再转车到平溪铁路线的始发站——菁桐,然后乘坐老式火车前往平溪。
……
抬头仰望着沈佳宜亲手写上自己的愿望、亲手放飞的天灯越飞越高,随风而去,逐渐混入其他人放的天灯之中,再也分辨不出。
靓坤说道:“这盏天灯飞的这么高,你今年的高考一定会考很好!”
沈佳宜说道:“谢你吉言,希望如此吧!现在天灯已经放了,我们该回去了。”
靓坤心想:好不容易才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怎么能就这样就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