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小说网>我竟是谋逆贼子的白月光 > 第二百五十三章 被人讹了(第2页)
第二百五十三章 被人讹了(第2页)
正当悬壶堂的生意蒸蒸日上之际,三月末的一天却突然发生了一出闹剧。
那日快到午时,有两三个病人正在一旁等着排队,突有一个人口吐白沫,两眼一翻,咣当一声到了地上。
在诊桌上替人把脉的山茗三两步走到了这人身边,给他搭脉,扎针,可这位的病情实在来得太过迅疾,山茗就算医术再好,也终究是无力回天,这人便在悬壶堂去了。
世间万事,生死本就无常,那日这位逝者的家人匆匆赶来将人带了回去。
本以为此事就此作罢,谁料隔了一天,这家人竟然将那人的棺材抬到了悬壶堂门前,就在门口哭天抢地,说是悬壶堂
医死了他们家亲人,要他们给个交代。
“义母,前天我也在,阿祖还没有给那人看病,那人就已经发作了,不关阿祖事的。”沛澜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有些无措地看着旁边的卫姝。
卫姝知道,这家人回去后必定是有人唆使的,让他们来搅黄悬壶堂的生意。
很显然,这也达到了那幕后之人的目的,今日的悬壶堂,一个看病之人都没有。
那些人穿着孝服,就在悬壶堂门口大声地哭丧,山茗听得脑袋疼,药堂内的几个孩子也俱是担忧害怕。
“沛澜,你带着你的朋友们去帮我找几个人!”
卫姝附在沛澜耳边同他说了几句悄悄话,再拍了拍他的脑袋,便让他们出门了。
外面那群哭丧的和围观的百姓见悬壶堂里面有人出来了,纷纷直起身子了看是不是悬壶堂当家的,谁料却出来了几个孩子,大家被勾起来的兴趣又缩了回去。
几个孩子前脚刚出门,后脚便见卫姝和山茗走了出来。
一见这当家的终于肯露面了,逝者那家的儿子连忙走了上来,指着两人的鼻子骂道:“就是你们悬壶堂医死了我老爹,你们得给我赔钱!”
“哦?”卫姝轻挑了一下眉,“你想要多少钱?”
“一百两银子!”
这家人的儿子狮子大开口,竟然要一百两,卫姝而今就算是将整个家底儿掏干净了都没有一百两。
卫姝厉声质问道:“你说我悬壶堂医死了你老爹,你
可有证据?”
那个儿子显然是有备而来,“我老爹就是从你们悬壶堂抬出去的,那么多人都看见了,你还想要什么证据?”
“你老爹是突发痫症,那日等在我悬壶堂,我爷爷还未给他看病,他便已经发作,此症来得又凶又急,你若是将你父亲的死赖在我悬壶堂之上,岂不是无稽之谈。若是你父亲突发急症死在了街上,你不是还要挨家挨户哭丧,要这条街上的百姓们都给你一个交代?”
没想到这女人竟然这般能言巧辩,那家儿子有些哽住了。
随即他脑筋一转,又说道:“你说我父亲是痫症就是痫症,谁又知道是不是你们将人给医死了胡编了一个借口。”
卫姝忍住了翻白眼的冲动,她再道:“那不然咱们就去见官,让官老爷评评理。”
要真闹上官府,这事儿不就藏不住了吗?这家的儿子就这般拖着硬是不愿意去官府,胡乱攀诬悬壶堂与官府有勾结,只要他们道歉赔钱。
真是泼皮无赖,卫姝这般想。
正当局面僵住之际,一个男人从围观的人群之外走了进来。
“你即说悬壶堂与官府有勾结,那咱们不若就去官府看看,究竟是不是你所说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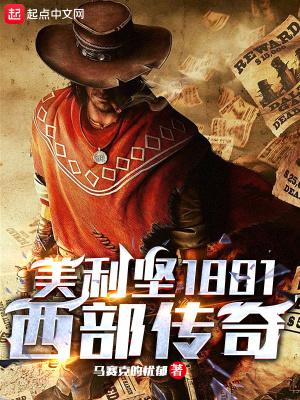

![女主一心搞钱[八零]](/img/819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