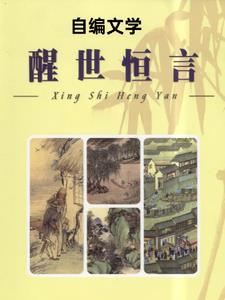02小说网>我与大鸡巴小姑的乡村土味日常 > 第5章 初行农事(第6页)
第5章 初行农事(第6页)
我的心脏漏跳一拍——她是在幻想我吗?
这个念头让我既羞愧又兴奋,下体渗出湿液,黏在内裤上。
小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喘息越来越重,健硕的腰肢开始不自觉地前后摆动,Q罩杯的巨乳随着动作上下颠簸,奶头硬得像两颗鹅卵石。
汗水从她紧绷的腹肌上滑落,在肚脐处积成一个小小的水洼。
巨根筋肉少女那粗壮的大腿肌肉绷紧,脚趾抠进湿润的泥土。
她的另一只手抓住自己左乳,粗鲁地揉捏,乳头被扯得变形。
突然,她全身剧烈颤抖,喉咙里发出闷哼。
粗大的巨屌猛地跳动,青筋蠕动如肥虫爬茎,龟头鼓胀得像拳头,马眼猛地一张,“噗嗤”一声,一股泛黄的白浊淫液喷涌而出,高压水枪般射进河里,滚烫的浓浊浆糊在阳光下划出一道弧线,像牵丝的蜂蜜般落入河中,冲得水面荡开淫靡涟漪。
紧接着是第二股、第三股…她像头正在配种的母马般剧烈喘息着,粗壮的手臂肌肉绷得像拉满的弓弦,精液一股接一股地喷射,直到河面上漂浮着一层乳白色的泡沫。
高潮过后的小姑像被抽走了骨头,巨屌软塌塌地垂在大腿间,龟头蹭着裤子,上面还挂着不少粘稠滑腻的浓精。
她瘫软在石头上,大口喘气,汗水顺着脖颈流下,在锁骨处汇成小洼。
片刻后,她睁开眼,羞赧地低头看了看自己沾满白浊的大手,突然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般红了脸,慌忙蹲下身用河水清洗。
水流冲走了大部分证据,但石头上还是留下了几处白斑,在阳光下慢慢干涸。
这个动作让她饱满的臀肉完全暴露在我的视线中,臀缝间隐约可见深褐色的肛门皱褶,像一朵羞涩的菊花。
她粗壮身影一晃,提上麻裤,裤腰卡在巨屌上,露出半截白花花的茎身。
她水润杏眼瞅了眼河面,嫩唇抿了抿,转身往田埂走,粗壮肉腿踩得水花“哗啦”响。
我屏住呼吸,等她走远,才从芦苇后钻出来,满身汗水黏得像涂了层油漆,腥臭味儿熏得头晕。
我悄悄后退,蹑手蹑脚地退回田埂,心脏跳得像要冲出胸腔。
刚才的一幕像烙印般刻在脑海里——可君自慰时迷离的眼神,她呼唤我名字时颤抖的声音,还有那根巨屌喷射时的壮观景象…这一切都让我既罪恶又兴奋。
回到田埂边,我假装一直在喝水,手却抖得几乎拿不稳水壶。
等我假装刚从田里走来时,发现小姑正蹲在河边洗手,她头发还湿漉漉的,衬衫重新穿好,但领口处明显多了一处水渍。
脸蛋仍然红扑扑的,眼神躲闪,裤裆里那根巨物似乎终于安分下来,软塌塌地垂在左裤腿里。
“洗好了?”我的声音干涩得像是三天没喝水。
小姑猛地抬头,水珠从她长长的睫毛上甩落。她慌乱地在裤子上擦了擦手:“走……走吧,王婶该等急了。”
我点点头,手里攥着水壶,不知该说什么。
太阳渐西,田间的雾气散尽,稻穗在风中沙沙响,像水流轻抚石面。
远处山峦模糊成暗影,山脚下的土坯房星星点点亮起灯火,炊烟袅袅升起,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乡野特有的潮湿热气。
青石村不大,三十来户人家像撒豆子似的散落在山脚下。
我和小姑沿着田埂往村里走,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小姑的巨大身影几乎能把我完全罩住。
路过村口的磨坊时,赵嫂正倚在门框上嗑瓜子。
这磨坊是赵家的,老赵头是个干瘦老头,整天光着膀子推磨,胸前的排骨根根分明,像晒干的柴火棍。
老赵头是村里出名的老实人,但他这儿媳妇却是个丰腴妖娆的美妇。
赵嫂三十八岁,是村里出了名的浪货,男人长年在外打工,她就成了脱缰的野马。
今天她穿了件碎花短褂,布料薄得能透光,领口开得极低,把那对G罩杯的巨乳勒得呼之欲出。
更要命的是她那两瓣安产型的肥臀,圆润饱满得能把裤缝撑开线,扭动起来像两团发酵好的白面团,村里光棍们私下都说,被她那屁股夹住的男人,没一个能撑过三分钟的。
见我们走近,她眼睛一亮,故意把两条白花花的大腿岔得更开,肥臀在木板上压出两个深深的肉窝,随即把瓜子皮往地上一吐,扭着水蛇腰就迎了上来。
那件碎花褂子绷得紧紧的,领口都快被撑裂了,露出大片晒成蜜色的乳肉,走起路来颤巍巍的,活像揣着两个灌满水的气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