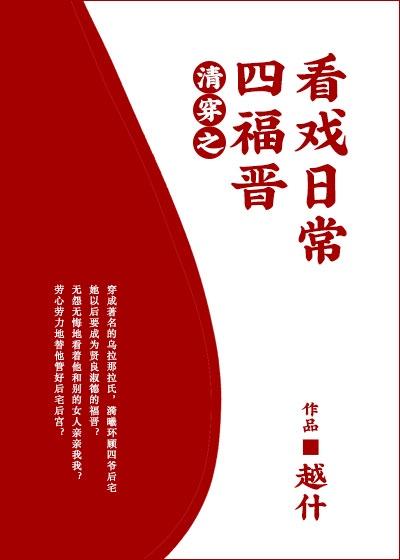02小说网>越界心动gl > 第九十三章 秋意渐近(第2页)
第九十三章 秋意渐近(第2页)
沈国康和于婉华,是典型的在社会主流轨道上行进了大半辈子的知识分子家庭。
他们爱女儿,但这种爱建立在传统的期待和认知框架内,期望女儿按部就班地完成学业,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在合适的年龄与一位同样“靠谱”的男性组建家庭,生儿育女,过上一种能被社会广泛认可、被亲友羡慕的“正常”生活。
“同性恋”这个词,对他们而言,或许在医学书籍或社会新闻里见过,但那始终是遥远的、属于“别人”的、带有些许负面色彩的词汇。
他们从未想过,这个词会与自己的女儿产生任何关联。
那是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嵌入骨血的社会规训,是他们对“幸福”和“正确”的全部想象。
撼动它,无异于撼动他们大半生构建的世界。
沈心澜能分析出母亲于婉华回避态度背后的心理机制,那是一种认知失调带来的强烈不适。当“女儿是同性恋”这个信息与她原有的信念严重冲突时,她的潜意识选择了最简单的应对方式——否认和回避。
不捅破,不直面,就可以假装问题不存在,就可以维持表面平静,就可以暂时不用去处理那排山倒海而来的震惊、失望、焦虑和恐惧。
作为心理咨询师,沈心澜太熟悉这套逻辑了。
在她的工作里,她不止一次接待过因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内心撕裂、备受家庭压力的来访者,也接触过那些同样痛苦、困惑、无法接受的家长。
她帮助他们梳理情绪,看见彼此的爱与恐惧,寻找沟通的可能,一步步走出情绪泥沼。
她懂得所有的理论,知道如何引导,明白需要时间和耐心。
可此刻,当问题切切实实落在自己身上,当那个回避的人变成了自己的母亲,那些娴熟的理论和方法,忽然间都变得有些苍白无力。
她知道该怎么做,可情感上那份沉重的无力感和隐隐的伤痛,却无法被专业知识完全消弭。
丁一察觉到沈心澜的情绪变化,知道自己可能说错话了,勾起了澜姐的烦心事,忙从沈心澜怀里抬起头。
“哎呀,澜姐,我瞎说的。你爸妈不接受、不喜欢我也没关系的。反正我知道澜姐喜欢我就行,澜姐爱我就好。我又不是跟他们过一辈子,我是跟你过呀。”
她说得轻巧,仿佛真的毫不在意。沈心澜知道丁一是在用她的方式安慰自己,也是在笨拙地为自己“减压”,表明她可以承受任何结果。
她捉住丁一在自己脸上作乱的手,握在掌心,另一只手却反过来捏了捏丁一的脸蛋,故意板起脸,眼底却漾着温柔的水光:“谁要和你过一辈子了?自恋。”
丁一先是一愣,随即眼睛瞪圆,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沈心澜!”
她连名带姓地叫她,佯装生气,一个翻身就把想起床的沈心澜重新压回床上,手脚并用地缠住,“你不和我在一起,想和谁在一起?嗯?说出来我听听?”
“你管我。”沈心澜笑着推她,却推也推不开。
“我不管谁管?”丁一不依不饶,低头去亲她的脖子,痒得沈心澜直躲,“快说,喜欢谁?爱谁?”
沈心澜顾忌着时间,连连讨饶:“好了好了,别闹了,我上班要迟到了……”
“那你说不说?”丁一撑在她上方,眼里闪着得意的光。
沈心澜看着她近在咫尺的、写满执着和爱意的脸,伸手环住丁一的脖子,将她拉低,在她唇上飞快地印下一个吻。
“喜欢你,爱你,行了么?丁老师,可以让我起床了吗?”语气是无奈的纵容,眼里却盛满了快要溢出来的柔情。
丁一这才心满意足,又重重亲了她一下,才松开手,笑嘻嘻地看着沈心澜红着脸匆匆下床,走向浴室。
日子在看似平静的节奏中向前滑行。
初秋的上海,是一年中最宜人的时节。天空是高远清澈的蓝,梧桐叶的边缘开始泛起一点点的黄。
早晚的风里带了明显的凉意,中午的阳光却依旧温暖而不灼人。
工作室的工作按部就班。沈心澜依然专业、耐心地接待每一位来访者,倾听他们的故事,陪伴他们穿越内心的迷雾。
丁一也忙碌着。新专辑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她常常在录音棚一待就是一整天。
国庆节前的一个周四下午,沈心澜刚结束最后一个咨询预约,正在整理今天的记录,手机响了。
“爸。”
“心澜啊,下班了吗?”沈国康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中气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