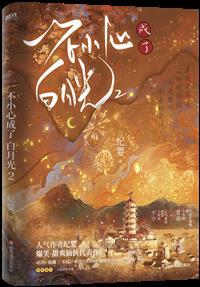02小说网>隋珠传 > 并蒂莲(第1页)
并蒂莲(第1页)
意识从一片温软的水汽与荷香中缓缓浮起。杨静煦睁开眼,恍惚间仿佛还看见那朵并蒂莲在眼前晃动,粉白的花瓣上滚动着清亮的水珠。
她眨了眨眼,梦境如潮水般退去,露出房顶熟悉的栋梁,和身侧人安稳的呼吸。赵刃儿仍沉沉睡着,手臂却维持着环抱的姿势,将她妥帖地护在怀中。
昨夜那个关于童年与执着的故事,像一剂深沉的安神药,不仅驱散了血色的梦魇,似乎还悄然打开了一扇通往更久远过去的门。那扇门后泄出的光与影,便化作了方才那场清晰得惊人的梦。
她静静看了赵刃儿一会儿,忍不住伸出手指,极轻地碰了碰对方微蹙的眉心,仿佛想将梦中那个“小花猫”的严肃与懊恼,在清醒的现实里全部抚平。
赵刃儿睫羽微颤,醒了过来。
“醒了?”赵刃儿声音带着初醒的微哑,手臂却下意识收得紧了些。
“嗯。”杨静煦在她肩窝蹭了蹭,声音里带着一丝柔软的雀跃,“我昨晚梦见你了。”
“梦到什么了?”赵刃儿随口应着,用手指替她梳拢睡乱的长发。
杨静煦却认真起来,微微撑起身,眼睛亮亮地看着她:“我梦到一个夏天,在东宫,咱们两个都是小孩。后园的池子里,开了一朵特别漂亮的并蒂莲,粉白粉白的,好看极了。我闹着要,你就把我放在池边的水榭里,自己提着裙摆下水去摘。”
赵刃儿拢发的动作停住了。
“那水好深啊,最后都没到你胸口了。”杨静煦继续回忆着梦境,手指无意识地比画,“水波晃着,我看着都害怕,可你还是稳稳走过去,把花摘了下来。我高兴坏了,就从水榭上跑下去接你,跑得太急,脚下一滑……”
她顿了顿,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就跌进池子里了。我在水里扑腾,看见你把刚摘的荷花一扔,慌忙过来捞我。后来我们俩湿漉漉地坐在池塘边,你头上、脸上都是淤泥和浮萍,脏得像只小花猫。我就看着你,一直笑,一直笑。你就板着脸,特别严肃地瞪着我。我就想,你真奇怪,为什么不笑呀?可能是我还不够脏吧……”
她忍不住笑出声来:“然后,我就从池子边捞了一把淤泥,抹在自己脸上。这下你可好,脸色都青了,更不笑了。”
杨静煦说完,笑着去看赵刃儿,却发现对方怔怔地看着自己,眼神复杂,有愕然,有震动,还有一丝极力掩藏的……痛楚。
那不是梦。
杨静煦的笑容慢慢敛去,她伸手,轻轻碰了碰赵刃儿的脸颊:“是真的,对不对?”
赵刃儿呼吸顿了一下,随即猛地别开脸,下颌线绷得极紧。过了好一会儿,才从喉间挤出一个短促而压抑的:“嗯。”
这反应让杨静煦的心揪了一下。她想起堂兄杨孚后来提起此事时,那毫不掩饰的迁怒与指责,以及赵刃儿当时沉默垂首,全然承受的样子。
“所以,”她声音放得更轻,带着迟来的明悟与心疼,“并不是像阿兄说的,是你贪玩疏忽。明明就是我让你去的,落水也是我自己不当心,你为什么不解释?”
为什么不解释?
赵刃儿呼吸停顿了一下。她转过头,目光与杨静煦相接,那里面翻涌着极其复杂的情绪。有被提及旧事的刺痛,有深不见底的自责,还有一种杨静煦此刻尚不能完全理解的失落与黯然。
解释?
如何解释一个死士让誓死护佑的公主在自己眼前落水?
如何解释那之后一连串的责罚、伤病、阴差阳错的分离?
又如何解释,正是从那个池边湿漉漉的午后开始,命运的洪流便将她们狠狠冲散,各自坠入了长达十三年的黑暗与煎熬?
那不仅仅是“谁对谁错”的问题。那是她一切苦难的开端,也是她最沉重无力的时刻。
“都过去了。”赵刃儿最终哑声说,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石缝里艰难挤出来。她显然不愿,也无法再深入这个话题,那底下是尚未结痂的旧创。她深吸一口气,迅速坐起身,背对着杨静煦开始穿衣,用行动强行截断了对话。
“该起了,今日事多。”
她的背影挺直,却透着一股拒人千里的僵硬。
两人默默穿衣,气氛有些凝滞。杨静煦正欲开口说点别的缓和一下,却见赵刃儿正低头绞着身侧两条系带,她系得很慢,很仔细,仿佛那不是一根普通的衣带,而是一道需要被严密锁住的闸门,以防某些汹涌的情绪泄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