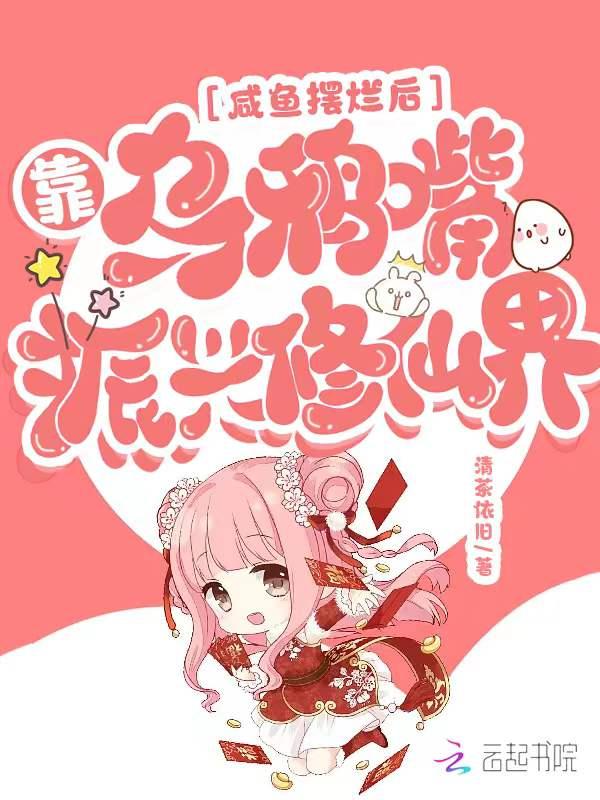02小说网>竟不还 > 90100(第21页)
90100(第21页)
何来顺被这一嗓子喊回了魂,受惊般转过头,就见船工旁边还站着名税场的津吏。
何来顺在渡口混迹多年,天天和这些负责稽查渡船的津官税吏打照面,自然认得这位税吏。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驻守在渡口的兵丁已经涌上前来拿人了。
被割喉的人从他怀里倒下去,何来顺惊慌不已,在一片兵荒马乱的钳制下百口莫辩,连那只檀木匣子什么时候抓在自己手里的都半点记不起来。
檀木匣子上赫然印着几根血淋淋的手指印,何来顺发誓他绝对没有想要这个匣子,但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何来顺就是为了争夺此匣谋财害命,且被税吏和船工人赃并获,当场擒拿。
说来也巧,盐船上那名割喉而亡的死者正是河东盐商洪氏,而此刻冤死大狱的何来顺,正是傍晚在酒肆刺杀税吏那少年他爹。
白冤一行本没打算管这茬闲事,却架不住苦主亲自“找上门”。
而这桩命案发生于半月之前,那津吏当场打开木匣,看见里头整整齐齐的一沓盐引后勃然大怒,直接怒叱何来顺为盗窃抢取盐引杀害洪氏:“这盐引是什么东西,岂是你区区一介下九流的贱民能觊觎的东西?!”
涉及盐引,这事儿就大了,何况还搭上一条人命。
何来顺当夜便从风陵津署的羁押房提到县衙大狱,稀里糊涂的经历过好几轮提审逼问,严刑拷打。
提审官吏从他是否在盗卖盐引,到是不是要贩卖私盐,继而又让他供出背后指使和党羽。
何来顺听得晕头晕脑,被折腾得生不如死,翻来覆去只有那几句毫无说服力的我没有我冤枉我什么都不知道。
可这在官府看来就是死鸭子嘴硬,不见棺材不落泪。
再一次行刑逼供完毕,狱卒将半死不活的何来顺扔进监笼时不住嘀咕:“果然是码头上的贱骨头,练的这身钢筋铁骨,扛得住县狱的大刑伺候,被折磨成这样了还是一个字都不肯招。”
何来顺悲哀的想,让他招什么呢?他什么都没做,也什么都不知道!像他这样的底层小民,根本连想都没想过那些,这些官吏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往他头上扣下数顶杀头大罪。
他认,是死,不认,也是死。
蝼蚁落到权钱手里只剩死路一条,他甚至连妻儿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真是不甘呐。
白冤担着何来顺的不甘和冤恨,扫量过他眼角未干的湿痕,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监笼,好似她从不曾造访此地。
世人的爱也好,恨也罢,都是天地间最为无形的力量,或成为羁绊,或成为枷锁。
而这人世间加诸于白冤的,从来都只是枷锁,亦或说这把携着冤恨的枷锁是她与这世间唯一的连接。
白冤踏着子时的梆子声现身衙署后巷,从一排排错落的低矮民居迈过去,便见岑寂的街头站着个身着青衣的男子,孑然立在县衙外的石狮旁。
屋檐下悬着几盏打亮的灯笼,光晕斜照在周雅人身上,将映照地面的影子拖得更长。
白冤忽而驻足,自不近不远处瞧人,他生得实在清峻,垂坠的青衫墨发随风轻扬,如水波浮荡出涟漪,无论行走坐卧都尽显端雅——似一缕轻拂而至的柔风。
然而此人看似如柔风,较量起来却毫不含糊,白冤见过他广袖挟风雷,折扇舞符刃,杀伐果决间不失凌厉绝尘之姿,事毕后敛尽锋芒,又端出这副温润如玉的做派。
更夫的梆子声穿巷过街的报着时辰,白冤脚下无声来到周雅人面前:“怎么找来的?”
他站客栈窗前目睹白冤再一次被冥讼所召,便立刻寻了出来:“若是冤死之人,大概率应该发生在狱地。”
继而他一路寻到衙署,果真没有料错,周雅人问:“怎么回事?”
“是那名在津渡刺杀税吏的少年,他那父亲已冤死狱中。”白冤抬步,与周雅人沿着长街往前行,将何来顺的冤案娓娓道来。
感知到这条路并非回客栈的方向,周雅人遥遥听见浪潮声,启口问:“要去渡口?”
此刻途径某户挑灯夜照的人家,烛光透过镂空的窗扉,拓下一副象征吉祥的繁复光影,至周雅人的侧脸上晃过。
“嗯。”白冤道,“去那艘商船上看看,应该还泊在渡口。”
繁华喧嚣的风陵渡在夜间沉寂下来,除却轮班值守的津吏和巡兵,只偶有几个人影在此地徘徊。
白冤和周雅人到时,正瞧见一名男子在栈桥上往津吏手中塞钱袋:“……还望官爷通融……”
津吏毫不容情的将钱袋扔回去:“少来这套,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辰,早就已经闭渡了,我若私放你过河,上头就得治我的罪。”
大端律令,擅启夜渡者仗八十,致人溺亡者绞。
“可是官爷,家母病危,我必须……”
甭管什么缘由,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若他今日放人离渡,安然过河便罢了,这事儿可能神鬼不知的掩过去,但若中途出了岔子呢?夜起风浪水涨船高,舟楫倾覆还不是常有的事儿,到时候追究起来,他必定罪责难逃,津吏不耐烦的搡开其人:“卯正启渡,莫要纠缠!”
白冤和周雅人走在河滩船只间的阴影里,轻易避开巡兵的耳目。
白冤道:“渡口也有宵禁?”
重愈千钧的十二道闭渡锁横于黄河,每一根几乎手臂般粗大,紧紧咬合在石槽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