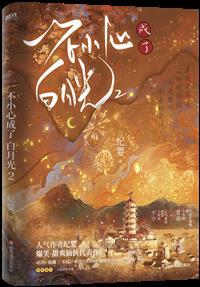02小说网>女穿男之太监求生记 > 第 70 章(第1页)
第 70 章(第1页)
山呼万岁之声如潮水般退去,金銮殿内重归肃穆。
萧衍端坐于御座之上,玄黑衮服上的十二章纹在殿内煌煌灯火下威严流转,他的目光扫过丹墀之下黑压压的臣工,掠过那些或恭顺或隐现思虑的面孔,最终,落向身侧那个垂手而立的靛蓝色身影一瞬,随即收回。
“众卿平身。”
早朝按部就班地进行。
各部院依序奏事,多是年关节下的例行公事:户部禀报各地钱粮冬赋入库情形,兵部陈说边关冬防布置,礼部奏请元旦大典仪程……萧衍或问一二细节,或直接准奏,处理得快速。
一切与往日并无不同。
但所有有心人都能感觉到那微妙的不同,御座之侧,那张多出来的酸枝木椅,以及椅子上那个过分年轻,面容沉静,甚至带着几分阴柔俊美的太监,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可偏偏是这种沉默的存在,比任何言语都更牵动神经。
司礼监秉笔太监郑保,稳稳坐在他的记注案后,笔尖悬于纸面,记录着朝议要点。他面色如常,偶尔还会抬眸望向御座,眼神恭顺。只有离他极近的人,或许能察觉他握笔的指尖,在记录某些无关紧要的条目时,会有一丝难以察觉的凝滞。
站在郑保侧后方的随堂太监周如意,则远没有这份养气功夫。他眼角的余光就像淬了毒的钩子,一次又一次地刮过关禧挺直的背脊和低垂的侧脸。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子,就因为得了陛下几分青眼,竟敢站到这等位置上来?御前伺候笔墨已是破格,如今竟登堂入室,立于朝堂,这让司礼监,让他们这些在御前经营多年的老人,颜面何存?
文官队列中,气氛同样微妙。以首辅柳文正为首的清流老臣,多数目不斜视,神色肃然,仿佛全然未察觉御阶上的那点变化,但紧绷的嘴角,蹙起的眉心,泄露了他们内心。
阉宦立于朝堂,本非正道,即便只是侍立,亦是逾矩。何况此人如此年轻,如此……貌若好女,难免让人联想到那些不堪的宫闱传闻。一些较为年轻的御史,已按捺不住,彼此交换着眼神,只待时机。
武勋队列则相对漠然,几位老将军眼观鼻鼻观心,他们对太监没什么好感,更关心边饷和冬防。只要不触及军中利益,皇帝身边多个把阉人,他们懒得置喙。
就在一份关于河道岁修款项的奏议即将结束时,一直沉默的萧衍忽然开口,打断了工部尚书的禀报。
“且慢。”
方俊义一愣,躬身:“陛下?”
萧衍的目光似是随意地转向身侧:“关禧。”
这一声不高,却如投石入水,瞬间打破了殿内维持的平静。无数道目光骤然聚焦,齐刷刷射向御阶之上那个靛蓝色的身影。
关禧面上沉静如故,向前半步,深深躬身:“奴才在。”
“方才工部所奏,去岁淮扬段河道岁修,实际支银几何?较之预算,是增是减?主要超支在何处?”萧衍的声音平淡,仿佛只是在考校一个寻常的书吏。
可这个问题,让丹墀下的方俊义额角见了汗。河道岁修,其中猫腻众多,预算虚报,层层克扣乃是常事,皇帝平日查问,多是宏观数目,何曾如此具体?且是问一个太监?
关禧微微闭目,脑中飞速运转。这些日子他整理,经手过无数卷宗,其中恰有工部近年的奏销汇总。他记忆力本就超群,加之刻意留心,那些枯燥的数字如刻印般清晰。
殿内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屏息等待着,看这个骤然被推到台前的太监如何应对。
不过两息,关禧睁开眼,声音清晰平稳地响起:“回陛下。据永昌五年工部奏销黄册所载,去岁淮扬段河道岁修,原预算银十八万五千两,实际核准支取二十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两有奇,超支两万八千四百七十二两有奇。超支款项,主要见于三处:其一,采买青条石料,因石质要求上乘,产地路远,单价较往年上浮三成,此项多支约九千两;其二,雇募民夫工食银,因去岁灾民多,以工代赈,增募两成,多支约六千两;其三,杂项物料及不可预见支应,计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两有奇。”
他一口气报出,数字精确到两钱,分毫不差,连超支的名目和大致缘由都说得清楚。
殿内顿时响起一阵压抑不住的吸气声。
方俊义脸色白了又青,青了又白。这些数字他自然心中有数,但被一个太监在朝堂上如此清晰地道出,尤其那最后一项含糊的不可预见支应,简直当众扇了他一记耳光。
他扑通一声跪下:“陛下!此……此乃……”
“朕没问你。”萧衍淡淡打断他,目光依旧落在关禧身上,“记得倒清楚。依你看来,这三项超支,可都合理?”
这已不是考校,简直是询问意见了,一个太监,竟敢妄议国家工政开支?
“陛下!”一名御史终于忍不住,出列高声奏道,“此乃朝堂议政,国家度支,自有户部、工部诸臣工详议,岂容阉寺之辈置喙?此例一开,恐非国家之福!臣请陛下收回此问,并令此内侍即刻退出朝堂,以正视听!”
有人带头,立刻又有几名年轻气盛的文官出列附和,言辞激烈,直指宦官干政,违背祖制。
萧衍面无表情地听着,指尖在御座扶手的龙首上敲击。
待那几名御史说得差不多了,他才缓缓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