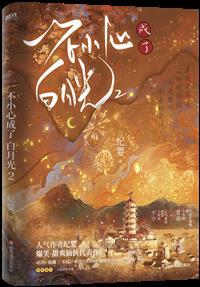02小说网>女穿男之太监求生记 > 第 71 章(第3页)
第 71 章(第3页)
“无妨。”关禧打断他,站起身,“带本督去看看。”
“是!督主请!”何璋连忙侧身引路。
关禧带着双喜和贵平,跟着何璋,穿过渐渐暗下来的宫道,朝着皇宫东北角走去。越走越僻静,宫灯稀疏,寒风凛冽。沿途偶遇的巡夜侍卫或低阶太监,远远看见这一行四人,尤其是走在前面那团在暮色中依然醒目得近乎妖异的绯红,无不骇然变色,慌忙退避躬身,大气不敢出。
东安门内北侧,果然是一片荒僻之地。高大的宫墙投下浓重的阴影,几排低矮敦实的库房黑黢黢地伏在墙根下。其中一间库房门前,挑着两盏新挂的气死风灯,昏黄的光晕照亮了门口。
一块崭新的,白底黑字的木牌,赫然挂在门侧。
“内缉事厂”。
四个颜体大字,筋骨嶙峋,力透木背,在灯光下泛着冷硬的光泽。虽说是临时赶制,却自有一股森严气度透出。
关禧在牌子前站定,仰头看了一眼。就是这里了。他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或许乃至一生,都将与之紧密捆绑的地方。
何璋推开厚重的木门,里面灯火通明。
最大的仓廒已被清理出来,地面扫得干干净净,墙角堆着新领来的被褥铺盖,虽然只是大通铺的架势,但在这短短时间内能做到这一步,已属不易。旁边两间屋子也按他所说布置起来,档房里摆了两张旧书案和几个空书架,值房里则是简单的桌椅。
那二十多个太监都聚集在最大的仓廒里,垂手肃立,鸦雀无声。见关禧进来,所有人齐刷刷跪下:“叩见督主!”
声音在空旷的仓廒里回荡,带着紧张的颤音。
关禧走到仓廒中间,站定。绯红蟒袍在众多灰蓝,靛青的服饰中,如同鹤立鸡群,也如同滴入静水的一滴浓血。
他没有立刻叫起,目光缓缓扫过每一张低伏的脸,似乎在努力记住某些特征,又像是在施加无形的压力。空气凝滞得几乎要滴出水来,只有灯花偶尔爆开的轻微噼啪声。
良久,关禧才开口:
“都起来吧。”
“谢督主!”众人窸窸窣窣地起身,依旧垂着头。
“地方收拾得不错,牌子也挂上了。”关禧的语气听不出喜怒,“这说明,你们有手有脚,也能办事。”
他停顿了一下,话锋陡然转冷:“但本督要提醒你们,也提醒我自己。从踏进这道门,挂上这块牌子起,我们的脑袋,就别在裤腰带上了。办的是陛下交办的机密差事,查的是宫闱内外的阴私鬼蜮。看得见的是荣华富贵,看不见的是刀山油锅。”
他的目光再次扫过众人,如寒冰刮过:“在这里,第一条规矩,也是死规矩——嘴巴要紧,耳朵要灵,眼睛要毒,心思要静。该看的看,不该看的,挖了眼睛也别看;该听的听,不该听的,割了耳朵也别听;该说的说,不该说的,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里。”
“陛下设此厂,是要耳目,要刀锋,不是要搬弄是非的长舌妇,也不是要首鼠两端的墙头草。若有人觉得,来了这里,是得了钻营的门路,可以脚踩几只船,或者想着给外面的哪位主子递个消息、卖个好……”
他冷笑一声,那笑声在空旷的仓库里显得格外渗人:“趁早熄了这心思。本督既能站在这里,就能让那些不该有的心思,连人带根,一起烂掉。厂规不容情,本督……更不容情。听明白了吗?”
最后一句话,如重锤砸下。
所有太监浑身一颤,齐声应道:“奴才明白!谨遵督主教诲!”声音比刚才整齐了许多,也多了几分真实的恐惧。
何璋站在人群前列,头垂得更低。
关禧将众人的反应尽收眼底,知道这番敲打暂时起了作用,他缓了缓语气:“明白就好。从明日开始,一切按规矩来。何掌班。”
“奴才在!”何璋立刻上前一步。
“你拟的那份清单,本督准了。尽快将所需物品领齐,安顿下来。另外,明日一早,所有人集合,本督要训话,立规矩。”
“是!”
“都散了吧,各自安顿。”关禧挥了挥手,不再看他们,转身走出了仓廒。
夜风扑面,他抬头望了望漆黑的夜空,几颗寒星疏淡。
回到乾元殿内那处新拨的院落,双喜和贵平早已备好了热水和简单的晚膳。关禧脱下那身绯红蟒袍,换上一件轻便的深青色常服。
用过晚膳,他回到书房。
双喜已经按照吩咐,找来了厚厚几大本《宫中则例》,《内监规条》以及历年有关宫人惩戒的案例汇编,堆在书案一角。
关禧铺开一张新的宣纸,提笔沉吟。
内缉事厂的规矩,绝不能仅仅是旧宫规的翻版。它需要更严苛的保密条例,更高效的运转流程,更冷酷的监察机制,以及……更直接只对皇帝和他这个提督负责的忠诚灌输。
他开始动笔,结合脑中那些来自另一个时代关于组织和纪律的模糊认知,以及这些时日对宫廷规则的深切体会,一条条,一款款地草拟。
灯火摇曳,将他专注的身影投在墙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