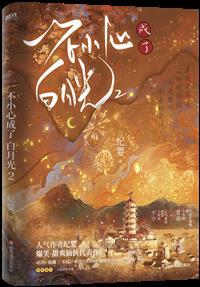02小说网>穿越之宜修 > 海军军歌(第1页)
海军军歌(第1页)
养心殿内,鎏金更漏的滴水声与翻阅奏折的沙沙声交织,构成了雍正处理政务时惯常的背景音。我坐于御案一侧,正将几份关于地方雨雪粮价的奏报分类整理,以备雍正垂询。殿内炭火暖融,却驱不散雍正眉宇间那因西北军需、河工度支、乃至新政推行中种种掣肘而凝成的沉郁。
苏培盛轻手轻脚地进来,低声禀报:“皇上,皇后娘娘,海军提督年羹尧在外求见,说是有紧急军务禀报。”
雍正从堆积的奏本中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锐利:“宣。”
年羹尧大步流星地走进来,一身簇新的海军提督官服还带着屋外的寒气,脸上却泛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混合了激动、震撼乃至一丝未及掩饰的亢奋的红光。他利落地甩袖打千:“臣年羹尧,恭请皇上圣安,皇后娘娘金安!”
“平身。赐座。”雍正示意,目光在年羹尧脸上停留片刻,已察觉到他情绪有异,“年将军,何事如此急切?可是福建、广东海防有变?抑或是……”他顿了顿,“赴英留学的将士们,有消息了?”
“回皇上,海防暂无大变,留学团亦在途中,尚未抵达英吉利。”年羹尧谢了座,却并未完全放松,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因刻意压制仍带着颤意,“臣今日急奏,是为另一事——前年遵旨,通过广东十三行及英吉利东印度公司,向英吉利国订购的那几艘新式军舰,头两艘,已于昨日抵泊天津大沽口!臣接到急报,连夜自京城赶赴查验,方才返回!”
“哦?到了?”雍正坐直了身体,我也放下了手中的朱笔。向英国购买军舰,是筹建新式海军、巩固海防的关键一步,也是顶着朝中不少守旧官员“以夷变夏”、“靡费国帑”非议推行的重要举措。如今舰船抵港,意味着计划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正是!”年羹尧重重应道,那压抑不住的震撼之色再次浮上面庞,“皇上,娘娘,臣……臣在西北多年,自诩也算见过些阵仗,雪山荒漠,万马奔腾,坚城巨炮,不能说司空见惯,也绝非轻易动容之人。可是今日……今日见到那英吉利来的军舰,臣……当真是大受震撼!”
他“震撼”二字咬得极重,甚至不自觉地挥舞了一下手臂,这在素来以沉稳果决著称的年大将军身上,极为罕见。
雍正眼中兴趣更浓,却也升起一丝疑惑。他了解年羹尧,此人能征善战,心高气傲,等闲事物难入其法眼,更遑论“震撼”。我见状,对侍立一旁的苏培盛使了个眼色。苏培盛会意,轻手轻脚地捧上一盏温度刚好的碧螺春,送到年羹尧手边的茶几上。
“年提督,一路劳顿,又乍见新舰,心绪激荡,先喝口茶,缓一缓,慢慢说与皇上听。”我温言道,既是体恤,也是让他平复一下过于激动的情绪。
年羹尧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连忙躬身谢过,端起茶盏,也顾不得许多,仰头咕咚咕咚灌了几大口,滚烫的茶水似乎稍稍压下了他胸中翻腾的惊涛。他放下茶盏,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叙述更条理清晰:
“谢娘娘。皇上,”他重新看向雍正,声音平稳了些,但眼中的震撼之色未褪,“臣在订购此舰时,只知英吉利海军冠绝西洋,其舰船必有过人之处。臣原想着,无非是船体更坚固,航行更迅捷,炮火更猛烈些,总归是海上的兵船,比咱们以前的福船、广船更合用罢了。直至昨日,臣站在大沽口码头,亲眼看到那巨舰缓缓驶入,才知……才知自己竟是坐井观天,想得太简单了!”
他描述着初见时的情景,语气中依旧带着难以置信:“那船……不,那不能叫船!简直就像……就像一座会移动的海上堡垒,不,是一座钢铁与橡木筑成的岛屿!巍峨如山,桅杆高耸入云!听那随船来的英吉利教官说,此舰在他们那边,称为‘一级战列舰’!船上,光是一层层的火炮甲板,左右两舷加起来,竟有一百零八个炮位!一百零八门重炮啊,皇上!”
年羹尧伸出双手比划着,仿佛想描绘出那庞然大物的规模:“这火力,说句不恭敬的,比咱们在虎门、在吴淞口修筑的那些最坚固的海岸炮台,还要密集,还要凶猛!这哪里是船,这根本就是一座能在大洋上自由移动、喷吐死亡火焰的海上炮台!臣当时站在码头,只觉得眼睛都看愣了,心头怦怦直跳,半响说不出话来!”
一百零八门炮的一级战列舰……我心中默念,脑海中瞬间浮现出穿越前,随导师在英国参观HMSVictory(胜利号)的情景。那艘纳尔逊的旗舰,正是拥有104门炮的一级战列舰,其庞大的体型、复杂的帆缆系统、尤其是那层层甲板上密密麻麻的炮窗,给人带来的视觉与心理冲击,确实无与伦比。那是风帆战舰时代的巅峰武力象征,是工业革命前夜人类工程与战争艺术的结晶。年羹尧的震撼,我完全能够体会。对于见惯了中式帆船的大清君臣而言,这无异于来自另一个维度的“巨兽”。
雍正听着年羹尧的描述,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御案,脸色也变得极为凝重。他或许无法完全想象那具体景象,但“一百零八门炮”、“海上炮台”这些字眼,已足够让他理解这军舰所代表的、超越当前大清水师认知的恐怖战力。这与他以往所知的“水师战船”,已是天壤之别。
我没有说话,只是看向身边陷入沉思的雍正,等待他消化这个信息。然后,我转向年羹尧,轻声问道:“年提督,这军舰体型庞大,炮位众多,固然震撼。但我想,它给你的震撼,恐怕不止于此吧?你是否登舰细看了?那火炮,那船体结构,乃至其运作方式,可还有什么特别之处?”
年羹尧闻言,看向我的目光中多了一分钦佩,仿佛找到了更能理解他震撼之处的人。“皇后娘娘圣明!确如娘娘所言!”他重重一拍大腿,“臣岂能只看个外表?当即就请那英吉利教官引领,登舰仔细察看。这一看,更是……唉!”
他摇头叹息,那叹息里充满了对巨大技术差距的无奈与焦灼:“别的先不说,单说那火炮。臣亲手摸了摸,掂了掂。那炮管,看着比咱们广东、福建炮厂铸造的红衣大炮,要薄上不少!可据那教官演示并解说,他们这炮,因铸炮的铁料更纯,工艺更精,炮管虽薄,却能承受更大的装药量,打出的炮弹射程更远,威力也更大!而且,因为内壁光滑,散热更好,同样连续发射,炮管升温更慢,不易炸膛,使用寿命也更长!皇上,娘娘,这……这还只是一门炮啊!”
他越说越激动,站起身来,在御前有限的空间里踱了两步:“窥一斑而见全豹。一门炮已是如此,那舰上其他的东西呢?那复杂的帆缆系统,能让如此巨舰灵活转向;那船舱内部的布局、水密隔舱的设计;还有他们操炮、操帆的那一套严整迅捷的规程……处处透着咱们没有的讲究!由此可见,洋人那边,领先咱们的,恐怕不光是船坚炮利,而是背后一整套的东西——炼铁、铸造、设计、操训……方方面面啊!”
这番话,如同重锤,敲在雍正心上,也敲在殿内每个人的心头。年羹尧不是迂腐文臣,他是实战打出来的统帅,他对武器、对军队的理解是直观而深刻的。他的判断,更具说服力,也更具冲击力。他看到的不仅是“器”的先进,更隐约触摸到了“器”背后支撑的“技”与“制”的差距。
养心殿内一片寂静,只有炭火偶尔的噼啪声。雍正靠坐在龙椅上,目光幽深,望着殿顶的藻井,久久不语。他登基以来,夙兴夜寐,整顿吏治,清理亏空,推行新政,自问也算锐意进取。可年羹尧带来的消息,却像一盆冰水,让他清醒地意识到,在另一个赛道上,对手已经跑出了很远,远到可能超乎他之前的想象。这种认知带来的,不仅是震撼,更有一种深沉的、混合了紧迫、不甘与巨大压力的复杂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