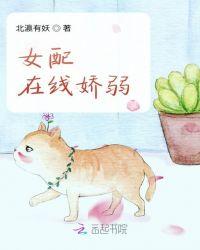02小说网>惊鸿宴 > Chapter 10(第4页)
Chapter 10(第4页)
刚想试着动一下僵硬的身体,一阵剧烈的眩晕感猛地袭来,让她眼前发黑,差点从椅子上滑下去。她连忙用手扶住冰冷的扶手,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
“该死……”姜宴兮低低地咒骂了一声,声音沙哑得厉害。她抬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触手一片滚烫。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昨晚被魏惊鸿那个病号给传染了。
想起魏惊鸿,心头那股复杂的情绪又翻涌起来。她用力甩了甩头,试图将那张脸从脑海里驱逐出去。
就在这时,一阵极其轻微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朝着她所在的角落而来。
即使没有抬头,她也能感觉到那道存在感极强的视线落在了自己身上。
她缓缓地、有些艰难地抬起眼帘。
几步开外,魏惊鸿正站在那里。
她已经换下了昨天那身被汗水微微浸湿的西装套裙,长发重新一丝不苟地挽在脑后,脸上的妆容也重新修饰过,遮掩了昨晚病态的苍白。除了脸色比起平时略显几分憔悴,她看起来几乎已经恢复了平日那个冷静、强势的魏氏总裁模样。
只是,当她的目光与姜宴兮对视时,那双琉璃色的眼里,还多了几分昨天之前从未有过的忌惮。
显然,昨晚姜宴兮那些话语,尤其是最后那个直白的质问,以及提出的最后通牒,并非没有在她心里留下痕迹。她或许依旧不认为自己有错,但至少,她开始意识到,眼前这个看似柔弱、一度被她牢牢掌控的女人,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轻易用物质和强权就能安抚或压制的小女孩了。
两人隔着几步的距离,无声地对视着。晨风吹过,带起姜宴兮额前几缕散落的碎发,也拂动了魏惊鸿一丝不苟的衣角。
最终,是魏惊鸿先打破了沉默。她往前走了一小步,目光落在姜宴兮明显带着病态潮红的脸颊和干裂的嘴唇上,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但开口时,语气却多了一丝近乎低声下气的试探:
“宴兮,”她叫了她的名字,而不再是“宴宴”,“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昨晚着凉了?”
姜宴兮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她,眼神平静无波,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湖水。
魏惊鸿被她看得有些不适,抿了抿唇,继续用那种略显生硬的、试图放柔的语气说道:“这里晨露重,你穿得太少了。我让人送你回房间休息,或者……去餐厅吃点早餐?”
她顿了顿,目光紧紧锁住姜宴兮的脸,声音压低了一些,带着一丝恳求:“跟我回去,好不好?跟我回去,回家。那里有最好的医生,有人能好好照顾你。你想怎么养身体都可以,我保证……不再像以前那样……”
她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很明显。她在示弱,在让步,在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再次抛出那个“回家”的诱饵。她以为,经历了昨晚的“坦诚相对”——尽管只是单向的质问和回避,以及姜宴兮最后那点未完全硬起的心肠,此刻或许是一个挽回的契机。
然而,姜宴兮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不用了。”她的声音依旧沙哑,却异常清晰,“我在这里很好。”
魏惊鸿眼中那点微弱的希冀之光,瞬间黯淡了下去。她的下颌线微微绷紧,显然在极力克制着情绪。她似乎想再说些什么,想再争取一下,但看着姜宴兮那近乎冷漠的眼神,所有准备好的说辞都堵在了喉咙口。
她知道,昨晚那个可以被自己的高烧和脆弱暂时软化的姜宴兮,已经随着晨曦的降临而消失了。此刻坐在她面前的,是一个清醒的、冷静的,并且刚刚被她传染、身体正不适的姜宴兮。而后者,显然比前者更难应付。
沉默再次蔓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尴尬而紧绷的气氛。
最终,魏惊鸿像是终于接受了这次说服的失败。她深吸一口气,退了一步,只是眼底深处那份不甘,依旧清晰可见:
“好。”她只说了一个字,停顿了片刻,才继续道,“那你……好好在这里休养。我过段时间再来看你。”
这话听起来像是寻常的告别,但落在两人耳中,却都明白其中的潜台词:我不会放弃,我还会再来,直到你答应跟我回去为止。
姜宴兮闻言,嘴角极其轻微地向上扯了一下,那不是一个笑容,更像是一个带着嘲讽的弧度。
她抬起有些沉重的眼皮,目光清凌凌地看向魏惊鸿,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像一把淬了冰的匕首,直直刺向对方:
“魏惊鸿,下次你来找我,我希望你带来的,要么是答应我的条件——把我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尊重我的选择,不再干涉我的生活。”
她顿了顿,看着魏惊鸿骤然变得难看的脸色,一字一顿地补充:
“要么……就是做好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准备。”
“除此之外,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这句话,彻底将魏惊鸿试图维持的表面平和撕得粉碎。她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眼里翻涌起压抑的怒火和被冒犯的寒意。她死死地盯着姜宴兮,胸膛因为急促的呼吸而微微起伏。
若是放在以前,听到离婚两个字从姜宴兮嘴里如此平静地说出来,她恐怕早已暴怒失态。但此刻,或许是昨晚的冲击余波未消,她竟然硬生生地将那即将喷薄而出的怒火压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