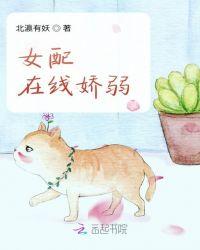02小说网>她分明是祥瑞 > 浪淘沙(第2页)
浪淘沙(第2页)
严湍话音才一落,便听见旁边“扑通”一声,安等华跪走几步,略带哭腔说道,“陛下!若是我大昭人人都像严御史一般居安忘危,西北失地该何时收复?!”
闻言,赵青在上,神色突变。
收复边地,是他的野心。
于是缓缓出声道,“安卿所言有理。”
闻言,严湍一党跪倒一片,附言道,“臣请求陛下三思!”
江沿本就站的笔直,周围的人都跪下去了,更显得他鹤立鸡群了。
同书见赵青始终犹豫,于是出言道,“此乃国家大事,并非是当下就能定夺的。”
同书话毕,赵青便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但政治独权也是,所以不能一股脑偏向一边。
见状,本来兴致勃勃的枢密使退到一边。
众多有权势的官员都在张望选童章或严湍哪边站,只有江沿看的真切,朝廷明面上两党对立,实则陛下与同书才是最大的控权人,在他们心里,两党势力僵持不下才是最有力的,若有一派被打击势弱,他们又会手动配平,他能进局,大概也是这个原因。
几番沉默后,有一谏官出声道,“臣要参侍中安等华私德不休,与其妻生母瞿氏有染。”
江沿只轻轻瞥过那人的轮廓,便知道他是昨日严湍宴会上的人。
众人看向安等华,后者满脸不可置信,双目瞪得溜圆,“你!你信口雌黄!”
只这一句,还不足以令他心神爽利,于是持笏就要冲上前打。
童章赶忙转身,抓了个空。
站在安等华身旁的礼部尚书李为梓眼疾手快地拉住他的手臂,可还是叫他重重踢了一脚,将那谏官踹翻在地。
倒在地上的谏官又不如意了,又作势要打回去,前排的大人站的站,跪的跪,后面的官员打人的打人,拉架的拉架,乱成一团。
“你有什么证据?!”
“我没证据会参你吗?”
……
江沿不知被这群人擦身多少次,依旧驻立在原地,丝毫未动,这到底是不是莫须有,其实没人在意,只要有谏官提出,这人的名声基本上就臭了,汴京以外各处州县,不知有多少官员因为许多莫须有的话被贬,这其中到底有多少为民而争,又有多少为权而争,也不得而知了。
江沿只能静候在不远处,等待着这场厮杀的血,何时能精准地溅到自己的身上。
面对如此混乱的场面,赵青烦躁地扶额。
“都停下!”同书站在大殿正中央的高处挥手制止。
无人理会……
“都~住~手——”赵青身旁的陈广华厉声呵斥。
宦官的声音就是尖锐,惊得同书和官家忙捂住耳朵。
下面的人果真就停下了,事了拂身去,陈广华退到官家身旁。
一众官员理理衣袖,跪回原地,还有些官员脸上多了几条抓痕。
严湍狠狠瞪了身后的谏官一眼,本是叫骂朝堂之上没个样子,结果那谏官自以为会意,又上前道,“陛下,臣以为左谏议大夫江沿对底层民生之事颇有看法,若陛下犹豫不决,可问江大人如今世况,可否利于出兵西北。”
来了,江沿心想。
听到这熟悉的名字,赵青从手里缓缓抬起头,朝下一看,立马就看见这位周身气质隔绝朝野的人,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依旧如松挺立。
官家没下令,任平眼神多刻薄,江沿也始终不发一言。
赵青喜欢有这样气质的臣子,他始终认为这是读书入仕的人该有的风度,奈何当今的朝堂生生养了一群莽夫,这也是他如此惦记杨铭筠的原因。
“江卿这是才回来?”此言是出自官家对臣下的体恤,已经晚了。
闻言,江沿出列,俯首作揖,回答道,“回陛下,臣昨日才至汴京。”
“这一路舟车劳顿,我很该放你休沐几日,来,上前来让朕瞧瞧,闵塘一行,风霜苦雨可让你变了样子。”
赵青话音一落,前面跪得乱七八糟的人立马往边上挪了挪,让了一条路子。